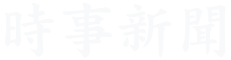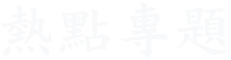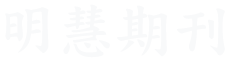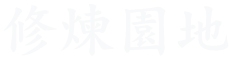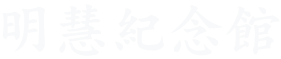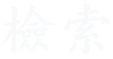難行能行 堅忍不拔
幾天前我在廣場上煉功,煉到第2套功法時突然傳來了刺心的自行車剎閘聲,微微睜眼一看,我曾見過的一名警察在不遠處瞪著我,當時我的心咚咚的跳了2-3次,我為自己還有怕心而感到難過。在修煉路上每次突破層次的時候免不了心跳,但當我堅持到底的時候,怕心就瞬間消失了,心變得很穩。第二天又一次被刺心的聲音心跳了一下,結果是清潔工的清掃聲。我堅持著,怕心沒有了。我每天早晨在廣場上煉功的目的,除了煉功之外更重要的是告訴人們「法輪功好」。
這一次警察闖進屋裏來,我想警察是來看看我在不在,說幾句就會走,那個警察副所長對我說「翻之前把書全都拿出來吧。」我想發正念,但心不穩。惡警開始翻,我在後悔沒有聽功友的話把我寫出來的文稿轉移。惡警把翻出的書、師父像、明慧資料,真象資料和文稿搶走了。我只拿了件半大衣就被他們拖到派出所,在3樓直接受酷刑,我除了洪法的話之外甚麼也不說。
他們把我的兩個手腕拽過去放了點紗布後上了手銬,手銬勒得很緊,不通血,然後固定在凳子下面的鐵上,又上了腳銬。兩個手不通血,腰疼,膀子酸。它們問我的生日,看我不搭理它們,便拿出搶來的身份證複印件登記。受刑的時候我仔細想了一想,覺得作為大法弟子不能消極承受,應該主動消除另外空間的邪惡,於是我開始喊:「法輪大法好」;「法輪大法是正法」;「師父清白」。他們顧不上登記,就想堵我的嘴,先是叫我停下來,看我不聽就打我。一個惡警握緊拳頭使勁打我的額頭;看我不動心,就開始輪班踢我;看還不行,就用塑料尺竭盡全力打我的嘴,塑料尺碎成3塊;它接著用拳頭打我的嘴,打得嘴流血。我暗暗想在過去的迫害中上額牙齒本來只剩下一個,最後一個都沒了,以後就沒牙咬飯了。但我繼續喊,最後它們用紗布擦了擦血,把紗布放進我嘴裏,然後用毛巾綁緊。雖然喊不出聲來,但我繼續念正法口訣。
這時我才看清它們是新上崗的警察,比以前還邪惡,它們想藉機「立功」得獎金,因此迫害更加殘酷。在這個時候不知是誰,用自己的鞋底猛打我的頭,我眼前直冒金星。已經熬到了深夜,肉體上的痛苦加劇,但每次背法,背正法口訣的時候痛苦就會減少,更重要的是要鏟除另外空間的邪惡。它們又開始堵我的嘴,然後在我頭上扣住塑料袋。背了幾遍法後開始喘不上來氣,這時它們才拿走塑料袋。夜更深了,它們使絕了招也沒能制止我背法,於是把我丟在刑具上,自己上床睡覺去了。
過了一會兒,綁緊了的毛巾滑了下來,能吐出字了,偶然間我又發現挪動腳步時腳銬也能發出聲音。於是我伴隨著腳銬的節奏背「洪吟」,還唱了歌,表達我堅如磐石的信念。「哪怕是野火焚燒,哪怕是冰雪覆蓋,哪怕是烈火焚燒,哪怕是雷鳴電閃,依然是志向不改,依然是信念不衰。」腳銬的響聲還有歌聲讓惡警驚醒,它們再次威脅我。時間一分一秒的過去,終於到了早晨上班時間。公安局政保科、610的人來翻看了搶來的大法資料和我寫的修煉文章後說道:「寫得像小說一樣挺有水平。」我還繼續念正法口訣,背法。一個約50歲左右的人,開始挽袖子發怒,它咬牙切齒的打我的額頭。快打,慢打,速度越來越快,我繼續背,因為頭向兩邊來回擺,只能傳出「嗡嗡」的聲音,手一停下來又恢復正常發音,最後惡警沒招了,再也打不動了,就坐在一邊看資料。過一會看了看我的手說,雖然腫了,黑了,但問題不大,這樣我從晚上8點到第二天9-10點左右一直戴著手銬、腳銬坐在刑具上受迫害。等到打開手銬時,手又紫又黑腫得老高,腰,肩疼痛難忍,我倒在了地上。就是這樣它們還是不給打開腳銬。
到了中午他們開始吃飯,叫我吃,我搖了搖頭,我決定絕食抗議。到了下午,我口渴了,再也喊不出聲音來,它們就開始問話,說甚麼只要說出資料來源就讓你馬上回家,它們還嘲笑我,說你應該是輔導員了吧?一年前去勞教時我就否定一切堂堂堂正正的回了家,一年後好多大法弟子走過來了,它們就說我是「輔導員」「站長」等話,其實我連那麼想見的在勞教所一起堅持下來的我們地區同修都沒有見過面。我加強正念,甚麼都不說,甚麼都不寫。但它們手裏拿著說是我的審問筆錄的東西,後來才知道是從我妹妹那問來的一些個情況,他們就隨便寫上的騙人的東西。剛上任的那個想從一個老太太那撈取政治資本的惡警已無法達到邪惡目的。下午過了很久拿來了「判決書」,有甚麼用?我連看都沒看就推到一邊去了。後來想:看也無妨,找過來一看拘留15天,有一瞬我想15天的話不用絕食不用遭罪也行……不!我決定像個師父的弟子那樣,不配合邪惡,絕食抗議非法關押到底。沒想到在車上惡警叫道:「你以為就這樣順利的放過你嗎?『扒──皮』!」一會兒又換了新惡警,我又被拖到市局8樓。它們聲撕力揭的喊「扒──皮」,把我拖到一邊,左手在上,和頭成20-25度角的地方固定手銬,右手在和頭大約75-85度角的另一邊的櫃上固定手銬,左腳用腳銬在暖氣下面固定,兩腳分開約成30度角,右腳用布綁著讓腳尖著地固定在櫃下面的橫樑上,喊完「扒──皮」就走開了。過一會回來對我說:「你能堅持到明天早晨八點嗎?」我仍一言不發,看見鐘錶指下午4.50分,大約是從4.45分開始吊起來的,才過不久但由於在刑具上已經坐了一夜,一整天沒吃東西了,我的手還腫著,因此難受至極,難以堅持。換了姿勢把脫掉的鞋費了好大勁穿上後好了一會,但還是一個樣。
我想起了在勞教所一宿一宿被罰站的一位女大法弟子。我只知道她非常堅定,當時我在絕食抗議,好幾次看見她被罰「面壁」。她後來被迫害死了。我想一定去了好地方,但還是止不住流淚,她是多麼的了不起呀,她那麼年輕而健康的身體被折磨致死?她罰站時該承受多少痛苦啊!
一個小時過後惡警變換手法了,假裝親熱的說,「你說吧。你說就馬上放你坐椅子,說不說?」我已經是沒有力氣說話了,眼睛也睜不開了,但還是搖了搖頭。說是一般只能堅持一個小時,我已經堅持了三個小時十五分鐘,開始吊我的惡警走了,換了新的。我要求上廁所,一放下來我就倒在了地上,起來後去了廁所,沒過幾分鐘又把我吊起來了,這回只把右腳放開了,二臂抬著還穿了半大衣,它們把扣扣得嚴嚴的,既熱又渴,簡直要瘋了,我要求喝水,它們說,說了才給喝。我想,不能給自己修煉的路上留下後悔!絕對不能說!我最大的幸福是在圓滿的路上看到師父的笑容,師父已經為我們承受太多了啊,我咬牙堅持著。又過了3個多小時。到了12點,看守們吃方便麵,叫我吃,我不理他們,這才給我鬆手,我就地倒下,好像是暈過去了。不知過了多長時間,我被「別睡」「別睡」的聲音喊醒,看我不吃,又吊起來了,我要求上廁所,惡警說只能去一次,你已經去過了,所以不行。接下來把右手手銬鬆綁,只銬左手,雖然難受,但比銬兩手時不那麼熱了,過了一個小時換了一個高個子和第一次吊我並喊「扒皮」的那個惡警,還是那麼邪,說:「這麼能行嗎?」「扒皮」又把我的右手銬住,到了2點好不容易去了廁所,原打算就算是廁所的水也要喝,但惡警根本不給時間,結果一口也沒喝上。回來後惡警假裝笑臉套近乎,我搖頭表示沒有要說的話,惡警氣壞了,把我吊起來後去了別的屋。
一個警察進來後講:「曾抓過一個大法弟子,科學上驗證癌症確實好了,這是事實。別撒傳單在家偷偷的煉吧。」這麼好的東西想和大家共同享受,反遭苦刑這是甚麼世道啊?!另一個警察不解的問我:「為連見都沒見過的師父如此的堅定,你和師父到底是甚麼關係?」是的,我99年2月才得法,從未見過師父,每當聽到國外弟子見到師父的時候,我就流淚不止。常人以為師父在美國「享福」,可我們弟子是知道的啊,師父是多麼的辛苦!只要不死,我就是堅修大法,堅信師父。不知為甚麼,那個喊「扒皮」的警察開始隔一段時間餵我一點水。
到了第二天4點鐘,看守又換了新的,來人假裝很和氣的樣對我說:「這麼多的傳單為甚麼沒發出去啊?都發到甚麼地方去了?給誰了?」我甚麼都沒有回答,我的左手被手銬銬得破皮了起了水泡,還出了一條條的紅線。我說:「我的手破皮了。」警察給打開了左手手銬。我說要喝水,警察說:「說了才給喝。」我搖頭。那個惡警上外面轉了一圈回來就問喝不喝水,我說喝水,惡警就叫我說,如此的重複多次。就這樣一秒一秒的煎熬著,好不容易到了早晨6點,我再一次要求上廁所,一到廁所我就奔水龍頭想要喝水,誰知他們跟上來輕輕地撞了我一下,我支持不住倒在了地上。他們說我是裝的,硬是不讓喝,我只好把雙手放進便池內接水喝,這才好過一點。回來後它們怎麼問我也不回答。最後,給了我一點誰喝剩的礦泉水,我用左手費了好大勁才喝下去,因為我的左胳膊被銬得用盡力氣也只能抬到耳根下面,又換了看守。終於到了8點,但它們還是不解開手銬,我只有一念──那就是堅持到底。到了8點15分警察把椅子拽過來坐在我前面說道:「你一天這麼難受能堅持多少天?」「到死為止!」警察無奈地拿下了右手手銬,我就地暈倒了。中間幾次加上廁所放下的時間我被吊十五個小時三十分鐘。到了9點他們把我弄醒後再吊50分鐘,扣除從8點15分開始休息的45分後,我被吊了十六小時二十分鐘。隨後,警察帶我去了拘留所。
到了拘留所後,警察根本不提迫害之事,反倒誣蔑我,我突然看到鏡子上的我,也把我嚇了一跳。打開著的頭髮散亂著,額頭被打得腫老高,把眼睛都給蓋住了,黑黑的臉一點人樣都沒有。雖然多次被抓,但這個拘留所還是第一次來,刺耳的鐵門聲、男人的嚎叫聲,讓我沒修好的一面暴露了出來。我感到有點顫抖,拘留所裏被關押的年輕犯人們(都還是孩子)雖然說我像鬼嚇得直躲,但因管教有令,叫她們脫下我的衣服仔細檢查,就一個勁摧我,我說:「你們不知道法輪功不撒謊嗎?甚麼也沒有。」聽了後,她們點頭。這是誰都知道的事實。我已經決定堅持堂堂正正的煉功,雖然左手根本不好使,但能做到哪就做到哪。我一煉功,犯人們說煉功的話管教來潑水。潑水算甚麼,我坐在管教走過時能看得見的地方煉功,不放過每一個管教和行人走過的機會。管教穿鞋進屋抓著我的頭髮往下拽,罵道:「這是甚麼地方?敢煉功?這是強制的地方。」我繼續煉。管教穿皮鞋踩我的手,煉功動作停了下來,當惡警管教一鬆手,我就繼續做煉功動作。管教只好走開。以後每次管教來時和管教與人談話時,我就堅持煉功。再也沒有人管我了。怕心不見了,心變的很穩。
第二天,管教叫我過去,本來我不想配合,但為了不給在我被打時靠牆站著嚇壞了的孩子們(年輕犯人們)留下法輪功不好的印象,於是決定去。是女監房對面的有桌椅板凳鐵窗欄的屋,可能是審問的地方。管教用非常親切的口氣問我出生年月日,還問:「警察打你了?」我沒回答。她說:「為甚麼在派出所回答而在這不回答?」我說:「都一樣!」
管教說些「我不讓你煉功了嗎?」等話想套我說話。我就是不配合。氣得管教抓住我的頭髮打了兩下,立刻停下來說道:「不回答是想要德,我為甚麼給你德?不給就是不給。」然後問我「你看看吧,可以給你戴手銬在鐵窗上罰站,也可以讓你一直這麼坐著,你能堅持多久?」「到死為止!」我只回答這麼一句。氣得管教把我從板凳上拽下來自己出去了。我坐在地上沒動,管教進來後讓我回去了。
9月1日被抓,1日2日遭受嚴刑逼供的迫害後3日上午進了拘留所。從那時起,我絕食絕水,9月8日的上午開始遭受野蠻灌食迫害。這時,年輕的同修銀月被抓,和我在一個監室受迫害。她是個年輕的媽媽,非常堅定。她給了我許多幫助,我連換洗的短褲都沒帶,又沒有錢,還趕了個例假期,要是沒有她,真不知該怎麼辦才好。特別是她不僅給犯人們洪法,還力所能及地幫助她們,她們都很喜歡銀月。在不配合邪惡方面,她做的很好。雖然她是後來的,但灌食時她是用擔架抬進去的,而我是被拖著進去的,回來時才輪上個擔架,她先走出了拘留所。我繼續受灌食迫害,灌食時那些大夫護士諷刺的說:「如果是戰爭年代的話她是個真正的英雄。」還互相說一些台詞取樂。他們因為知道我不是第一次被關押,所以不問我堅不堅持,並表示佩服。可能是9月10日送我去大醫院檢查後打了2瓶點滴,我又餓又難受,連覺都睡不著,海菜湯味撲鼻而來,我好想喝。
那時我想起了勞教所兩塊冰糖的故事。我有一次在看守所絕食抗議12天後回家,第18天就送往勞教所。身體尚未恢復,加上因為不寫決裂等受惡人群起圍攻。因此我的身體很糟糕,臉色可能很嚇人的,因膽囊不好常常感到饞、難受。有個被逼迫下違心「決裂」的回族女學員偷偷的給了我兩塊冰糖,是繞著一個人的後背遞過來的,連錢都沒有的我不知有多感激,這哪是兩塊冰糖啊,是她被逼迫妥協的內疚的心啊,是對苦難中的我的支持!
幾天的迫害中我的兩手大拇指及左腳大拇趾麻痺了。在艱苦的環境中,在難忍的時候,我用心背師父的法──「難忍能忍,難行能行」,難才能修,不難就修不了。
綁架第16天的時候,它們叫我準備東西回家,這幾天中,每天早晨惡警們都怕我死過去,而悄悄揭被看看,並命令犯人輪流守護。我穿上外衣就完事,可是有種奇怪的感覺,管區民警和家屬都沒有來。犯人背我上了車,在市公安局換了一輛車,原來它們是帶著我直奔勞教所或監獄。路過水果店時,下車買了些水果叫我吃,還讓我喝水。我搖頭,我連說話的力氣也沒有了。「不吃也沒用了,吃吧。」我仍然不配合。歷經2天的嚴刑逼供,絕食絕水5天和折磨灌食8天後,現在又坐小車去省城的肉身痛苦至極。嘴唇裂了,胸腔火辣辣的,真想用手撕開。身體來回晃,看著水還不能喝,只能咬牙堅持。我決不能在邪惡面前表現軟弱,死算甚麼?死並不可怕!作為大法弟子,就是死了也是幸福的。不過當時的那種痛苦是難以形容的,當時我想,大法弟子不能自殺,雖然我看不見師父,但我們不是知道師父看護著我們嗎?深信師父的巨大慈悲和智慧嗎?我只能忍,只能堅持。回過頭來想想,人也有比這更痛苦的事。癌症患者去世的時候要經歷比這更難熬持久的痛苦,所不同的是他們沒有其它選擇。可是在明擺著的道理面前,在痛苦的時候,我有時也會不知不覺的想:師父啊!我可能是個達不到師父要求的不爭氣的弟子呀,可能修不上去呀……這樣為自己辯解。但想起大法弟子的責任,想起師父的慈悲苦度,又咬牙堅持。不是層次的問題,而是我決不能讓師父失望。
下午4點左右我到達勞教所。管理科科長作出很失望的樣子問:「她怎麼來了呢?」一年之前我曾在這個黑窩受迫害一年,那時我堅持絕食抗議。這次來勞教所後,我沒有怕心,心也不跳,很平穩。好不容易來到門口後,我就坐在地上不走,警察無情的拽我進去,我就拼命喊疼。他們把我抬到床上,醫生和護士喊著我的名跑來了。「她又怎麼了?」我閉上眼睛不回答,要給我做心電圖時,帶我來的警察說路上一口水也沒喝,絕食2天。我想我得揭露謊言,於是我說「我十五天絕食,身上全疼。」「你到這吃不吃飯?」「不吃!」大夫看到道道血印、又黑又紫的手脖和不好使的胳膊,問警察是怎麼回事?警察只回答「手銬」兩字。其實他們也不知道是怎麼回事,安靜了一會。我聽到他們的對話「9月1日抓,今天正好15天,15天絕食能活著?」「灌食了。」其實我能活到今天已經是超常的了,過了一會,有人進來喊到「回去了,回去了,不要你了。」送我來的警察也進來問我,要送你回家,但需要寫個「不煉」才行。我說:「不寫!」「要回去了,吃不吃飯?」「不吃。」「那送到兒子那吃不吃?」看來勞教所知道我兒子在省城。我點頭後,他們要我在這等他們,把兒子接來,但勞教所不想留我,我也表示一起去。
他們問我兒子的電話,因為來新生的時候大學學生的電話號都有變化,因此我不知道。我們只好去學校找我兒子。好不容易找到了學校保衛科,就是找不到。原來兒子班裏的同學齊心協力的讓兒子避開了,每每警察因為我的事來找他時都是要錢。我兒子很可憐,5歲時父親去世,根本不知道甚麼是父愛,唯一的媽媽拖著有病的身體,成天忙亂的為解決生活費危機而奔波,因此家裏的一切就得靠他支撐。11歲開始,衣服也是自己洗,初中時讓他做家務時說:「你是戶主。」他以為自己真是戶主。有一次,看戶口本後說:「原來以為我是戶主,不是啊。媽媽是戶主。」弄得我大笑一場。修炕,劈柴,挖下水道等活都得孩子假期做。上大學後因為媽媽有時被叫到勞教所,還得從好不容易湊來的生活費中付灌食費,再難他也沒有一句怨言,還對管教說:「不要打我媽媽!」今天就這個樣子,還得找兒子。最後,還是我給兒子同學掛電話,同學確認後兒子才出現。從此,兒子背我走動。那天晚上喝了一個酸奶,3口牛奶和水,但回來時一直在吐,多虧兒子給開窗戶在一旁照顧才過得去。這樣9月1日被抓後9月17日下午4點回家,妹妹見到我後說「這一次傷害最大,比在勞教所絕食抗議56天時臉色還差。」就是回到家後前幾天吃飯都很費勁,喝牛奶就吐,喝蜂蜜也不管用。現在我在師父的呵護下基本恢復正常吃飯。剛出來時,左胳膊疼的伸不了,就是現在兩拇指和左腳趾雖然還處麻痺狀態,但我相信有師在奇蹟會發生的!
按照常人的想法,邪惡對我的迫害,表面上看是新上崗、新上任的警察想立功,撈取政治資本。從修煉的角度看,從法理上看,是因為我有執著心,好像是修過來了,但還放不下執著。這個執著去了,又跳進了另一個執著。就連怕心也是修下去了,然後又產生了,還沒完全修好。回過頭來看這一切,都是一瞬間的事,就像一場夢。修煉路再難,只要我們能把人心放下,把自己當作大法弟子的時候就能放下自我,其實甚麼都能過去。有些難是自己的雜念造成的,弟子感到慚愧。
是師父呵護弟子闖過了難關。在派出所,我在刑具上很艱難的時候,感受到了另外空間的我在結印煉功,弟子會萬分珍惜師父的苦度,做好應該做好的一切。回家後才知地方警察早就預料到勞教所不會收我,但它們不甘心,想在煎熬中逼迫要「保證書」,聽說從我家到省城近1000公里,回來的路上它們也一直在問,有一次難受的說了一句「說煉還是說不煉有甚麼關係?」不對!我馬上悟到這不符合法理,便說道:「死了也煉!」惡警不再問了,叫我在家煉。
回家後沒過幾天管區民警來了。當時我正在寫這份材料,我從家出來,就在有人的地方說道:「你看我的胳膊和殘廢差不多少,這符合法律嗎?」管區民警遲疑了一下說道:「那手脖子是上邊幹的,不是我幹的。」「這肩老掉,這是你的事。」警察沒說幾句就走了,再也沒來。過幾天治保主任來了,我說疼,但他不理,說道:「因為你在廣場上煉功,影響不好,不要煉了。」我說:「我現在就是胳膊疼,以後我還要去煉。」後來我才知道,我是因為煉功才被抓的。10月11日起,雖然胳膊還疼,有些動作做不完整,但我又開始在廣場上煉功。有時遠處傳來罵聲,但我沒有停止,我會修煉到底的,同時救度一切可救之人。
由於層次有限,表達能力差,有不對的地方請同修慈悲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