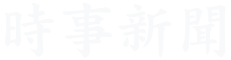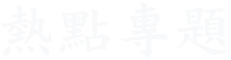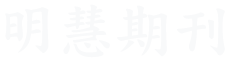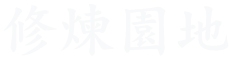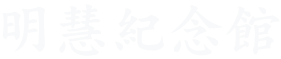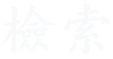河北省衡水市阜城縣劉素香遭酷刑折磨
1999年7.20邪惡對法輪大法及大法學員開始公開的迫害。8月崔廟鎮政法委把我抓去逼我寫不煉功的保證書。因不寫保證,我被送往阜城縣公安局。一進門,政保股長魏召田就指使幾個惡徒打耳光,我被打倒在地,於是大聲喊:「打人啦!打人啦!」政保股辦公室在二樓,樓下屋裏的人都跑出來仰面觀望。魏召田掐著我的後脖子,兩惡徒在後面推搡著弄上了樓。我被打破了鼻子,白褂子前身全被血染紅了。
11月中旬,我去北京證實大法,在天安門廣場被抓捕。公安局的惡警們把我一手從肩向下一手從後向上銬住(叫「背銬」,也叫「二郎背山」)緊銬子,然後在手與背之間墊大法書、酒瓶子;把大法書一張張撕下往我嘴裏塞,胳膊像掉了似的疼痛,冷汗把衣服全都濕透了。我被迫面向牆站著,頭不能抬起來,他們用細鐵棍不停的抽打、踢;他們在背後一踢,我的頭就撞到牆上,踢得越猛撞得越狠。約7小時後鬆開手銬,我的胳膊、手指頭都不會動了,手的厚度是原來的三倍,手背成球面狀,手腕的深溝寬如小指,往外滲黃水。我一天沒吃飯也沒喝一口水。
晚上,把我送到一個像是臨時拘押大法弟子的地方,兩人銬在一起。次日天剛亮阜城公安局的人就到了,政保股長魏召田對我滿口流氓話,大罵不止。在縣拘留所關了一個月,罰了3000元錢。我從拘留所出來好像都不會走道兒了,在回家的路上,遇到了母親(大法弟子),告訴我小弟和大弟媳去北京證實大法被抓回來,罰10000元贖人,指著旁邊三個騎摩托車的人說:「看,等著拿錢呢!到哪去借啊?!我被釋放出來借錢,罰我200元。」
2000年3月的一天晚上,我在看《轉法輪》,鎮政法委書記曲東武、執法隊長劉元才等六、七個人闖入我家,把我綁架到汽車上,11歲的兒子和兩個女兒站在車前哭著央求不要帶走媽媽,鄰居老太太也求情,都無濟於事。途中曲東武問我:「還煉不?」我說:「煉。」
我到鎮政府被打後,關到一間屋子裏,屋子裏面僅有一張床也搬出去了。此日早晨,不修煉的丈夫去問情況,被關到車庫裏。三、四個惡徒用笤帚對我邊打邊問我煉不煉, 笤帚把兒打沒了,只剩下頭才停止。下午,他們脫去我的棉襖、鞋(被抓時不讓穿棉褲和襪子)、光著腳,我穿著單褲、單褂和大曹莊的同修紅維站在南牆北面陰處凍了半天,凍得發抖,就煉功抱輪。以後每天從早晨到上半夜都這樣。第三天下午,三個惡徒用刷子鑿我腦袋,到後來我也不知道疼了,都木了;又拿著熱水瓶在我頭頂上威脅要用開水澆我。後來村幹部到鎮上說我家的棉花地裏的草把棉花都吃了,要求放我回家,因我不配合邪惡要求,他們不放我。這次被非法關押5天。後來又因為我簽名向全國人大反映法輪大法真象被抓去折磨兩天。
2000年5月初,我和妹妹劉建新去北京證實大法。農曆四月初八上午8點多鐘,在天安門廣場被抓,送到現在的天安門公安局。下午崔廟鎮鎮長劉新榮、派出所所長王秋生到北京押解我們姐妹倆,王秋生對我連罵帶侮辱,很下流,一耳光打破了我的鼻子,血一滴接一滴的流。他又藉機侮辱,把我和妹妹銬在一起,塞進車後面的工具箱裏,怕我們死在裏頭,不到300公里的路程,途中停車檢查兩次。
到鎮上,一下車,鎮政府大院內就圍上來了一圈人,對我們亂打亂踢一頓,之後把我們推到屋子裏,十幾個惡徒站一圈。我村的年輕同修鄭福勝被他們逼著跪在中間,我被他們像踢足球一樣踢來踢去,倒在誰跟前誰就再接著踢,踢一腳就問一句:「還上北京不?」踢一陣子後,用早已準備好的水泡過的木椅子腿打手心,眼看著手變成青紫色,臀部、大腿全都被打成黑紫色,跟茄子一樣。20多天後我的手像壞死了,還沒知覺,走路、坐都很艱難,坐下起不來。我的長髮亂得像瘋子一樣。妹妹說,看見我被惡警抓著頭髮往牆上撞。我自己已沒有這個記憶了,只覺得頭疼、麻木。他們折磨夠了,逼我趴在床底下,頭向外伸著,看他們打妹妹。妹妹被打、踢得在地上滾。惡徒們把我從床底下拽出來,弄到門外跪在直徑約5-6公分的棍子上,嘴裏叼著啤酒瓶子,瓶子掉了還打。屋裏還在繼續打著我妹妹和本村的同修張瑞珍。一小時後,把我弄到一間黑屋裏,一個醉漢用鞋左右開弓打我的臉,一邊打,一邊噴著酒氣問:「還煉不?」我的臉全腫了,眼也睜不開了,嘴也張不開。打完後,又把我送到一個地方,裏面關了很多堅定的大法弟子,大弟弟劉秋生也在裏面。我視線模糊,湊到跟前才認出大曹莊同修王素清、馬培芝,他們的臉腫得老大,再細看下去,原來這裏關的都是熟悉的同修,他(她)們的臉全變形了。惡徒們把被打得眼青鼻腫的大法弟子叫「熊貓」。同修們告訴我,他(她)們從昨天上午8點被折磨到今天凌晨2點,王素清被打得嘴裏往外流血。毒打後,惡徒們從頭上澆涼水,往身上潑水,叫我們跪棍,叼水瓢(裏面有水),端水盆等,用各種辦法摧殘折磨。
2000年7月,幾個惡徒又無故把我綁架到崔廟鎮政府,3天後關進阜城縣看守所,在那裏因我們集體背誦《洪吟》,把我雙手高舉銬在窗櫺上一夜,黎明前昏死過去才鬆開。甦醒後所長宋合臣又給我和同修吳金紅、時豔芬上吊銬。晚上死銬,無法洗臉、吃飯,好心的大姐馬憲英(不修煉)給我擦臉、餵飯、餵水果,我很過意不去。反銬時,我讓她把水放在炕沿上,我可以不用手端跪著喝。那裏從來沒讓人吃飽過,鹹菜很臭很臭。大家無法躺著睡覺,大小便也不給鬆銬,吊銬時,就更困難,小便由馬大姐和幾位好心人用盆接,大便時,馬大姐把兩個便盆桶摞起來,為避免男獄卒,用東西遮擋一下,這樣我熬過了6天6夜。
宋合臣不讓煉功,我說:「修煉人哪能不煉功呢?」他給我戴上腳鐐,逼我在院內趟鐐,牢裏面的人都把著鐵欄杆看著我,很多人向我伸出大拇指。走了7圈,我的腿上、腳鐐上都是血了(現在腿上還有疤痕)。從此我開創了自己煉功的環境。
我沒上過學,識字不多,請同修教我背《洪吟》、《論語》和經文,閉上眼睛看見眼前都是字。這期間丈夫來看過我一次,他看到我那樣子流淚了。他不會做飯,帶著三個孩子,又餵著牛,又忙地裏的活,面黃肌瘦。
9月我被非法判勞教2年,要送到河北省石家莊勞教所。臨上車前我問公安局的人我家人是否知道,回答說我家沒人接電話,其實我家從來也沒安過電話。丈夫拿錢到縣公安局去贖我,後來又聽說我被送石家莊勞教所去了,又到縣裏想把我弄回來,所花的錢、所罰的錢以及對我一次次的折騰,10000多元就這樣沒了,在我們這個貧困的農村這可是天文數字。
到勞教所,我被分配到四大隊。進隊第二天,隊長帶我去服裝廠,這裏被奴役的人們早上6點起床,工作到夜裏12點或凌晨2點,除了吃飯時間,就去當牛馬、當機器。我不幹,隊長問原因,我說家裏的活有的是,我沒犯罪,何必到這裏來幹活?她說:「這裏的衣服(勞教衣)你不穿,活不幹,你來幹甚麼來了?」我說我煉功做好人,我根本就沒犯罪!我不服從他們管理,到處走動。有一次同修傳看手抄師父經文被隊長發現拿去了,我從她手裏搶過來填到嘴裏。她說我吃了,氣急敗壞,把我銬在上下鋪的上鋪邊上,白天站著銬夜裏躺著銬兩天。
一天,我約同修們早晨排隊報完數集體煉功,隊長叫來男惡警兇惡的踢大家,把我拽到屋裏摔到地上,頭上摔出雞蛋大的疙瘩,我被銬在上鋪邊上9天9夜,每天只讓睡幾個小時。同修們見我被折磨,集體絕食反迫害。他們把我調到5大隊。5大隊已有20幾位同修先後絕食。為勾引我們的食慾,做好的飯菜,讓我們在飯堂排隊站著看別人吃飯。20天後,我和先絕食的同修身體已經很虛弱了,劉隊長(女)逼著我們把床從2樓搬到3樓,從3樓又搬到2樓,來回倒騰,打掃廁所,擦地,擦高處的水管、燈等,反正不讓閒著。
絕食一個月一天早晨,飯堂大門沒開,聚集了2000多人等著吃飯,我在樓口台子上煉功,隊長看到,把我往高處的管子上銬,先後用了三個手銬也沒銬上,他懷疑手銬壞了,只好銬在低處。那時我站立已經很吃力了。約過了一個小時,拉我強行灌食,5個人分別按著頭、胳膊、腿,「大」字形,仰臥在床上,用勺子壓住舌頭,鼻孔插胃管。管子插入氣管,憋的很難受,手又不能去拔管子,喊又喊不出來,全身動不了,痛苦的掙扎……我甦醒後,惡警接著又被繼續灌,很鹹。過後我全身發燒,都吐出來了,吐過後全身發冷,蓋兩床被子還抖作一團。監控叫來獄醫(女)看過說:「沒事」就走了。冷過之後發高燒,一位被灌過食的同修一夜沒睡給我冷敷,照顧。她絕食的時間也很長了,身體極度虛弱。次日起床時,我全身一點勁也沒有,穿衣服都很發愁,大腿還沒有小腿粗,骨瘦如柴,牙齦萎縮,連牙根都露出來了,發音很困難。惡警迫我去擦地,哪來到力氣去擦?一間小廁所很長時間才擦完,坐在裏面動不了。這場迫害之後,不再讓我們去食堂看人吃飯了,而是站著等人們回來,叫我們搬床,擦地,擦廁所等。
我絕食33天,被強行灌食6次,最後兩次是很鹹的鹽水,很多同修被灌過之後都吐。一天早晨起床後,我去放被、枕,發現那屋裏銬一位同修,已銬了一夜了。我把此事告訴了同修們,大家在樓道裏集體煉功抗議迫害。我和兩位同修被叫到隊長辦公室,一進門我就感覺進入魔窟了,隊長劉志英指使一惡徒用鍛煉身體的劍抽打一位同修的背部。我喊:「不許打人!」她衝向了我,用劍把子打我的頭,把我弄到樓底下站著(抬不起頭來)。折磨完那兩位同修後,把我叫上去,關上門,扒去外衣,接著就是這個一腳,那個一拳的圍著打,踹跪下,又踢起來。如此反覆好幾次,最後一次把我踹跪下用膠帶一層一層的把我嘴封起來,他們看著我狂笑。兩個男惡警戴上手套,用小手指粗的繩子從兩手腕螺旋往上纏到肩膀,再把兩小臂拉到背後向上提到肩胛上部捆住,無法用語言表達那種痛苦。黃豆大的汗珠往下流,全身像水洗的一樣。他們用橡皮棍沒頭沒腦的打。不知過了多長時間,解開繩子,我的兩臂已經沒有知覺,耷拉著不會動,小手指的深溝裏滲黃水。這種酷刑叫「上繩」。他們拿我兩手緩緩的活動者,時間不長又上第二次繩,酷刑後,同修們見我被折磨的慘狀都哭了。
同修們一直抵制奴役勞動,發展到罷工。一天早晨8點多鐘,我被叫到隊長辦公室,劉志英說是我操縱的,扒掉我衣服用電棍電,我不停的喊:「鏟除邪惡,鏟除邪惡!」她說:「我叫你鏟除邪惡!」電我的嘴、臉、頭,後來就不分甚麼部位的電,用橡皮棍打。電棍的電不足了,再換充足了的,換了充,充了換。我全身都軟了,一點勁也沒有,腦袋也呆滯了。啪啪的電擊聲,燒焦的皮肉味,橡膠棍子的毒打聲和惡警們的凶殘陣勢,這一幅幅恐怖畫面,構成了十足的人間地獄!
惡徒們還嫌不夠,又叫來上次給我上繩的惡警再次施「上繩」酷刑。劉志英說:「這根繩子特意給素香買的。」 繩子纏斷了,接個疙瘩再上。一直到中午打飯時這場殘酷的迫害才停止(現在左臂上仍留著繩索的疤痕)。他們不放我回宿舍,弄到他們值班室宿舍罰站,不許靠牆,不許睡覺,3天3夜,我進入昏迷狀態。劉志英趁機逼我寫不修煉的保證書,威脅說不寫還上繩,我不理它。她摟著我的肩膀到飯堂去,後面跟著兩個男惡警,一個手裏拿著電棍,一個拿著警棍,進裏後,劉走了,兩惡警逼問我寫不寫,我說不識字,它就用電棍電我的嘴。我的體力和精力超越了極限倒在地上,手也不知道甚麼時候破的,血止不住的流,電棍指著我的嘴繼續逼問,我斬釘截鐵的說:「不寫!珍惜大法就是珍惜生命!」我拼命鼓足全身的力氣喊:「打死人啦!」惡警們卻嚇跑了。這次被折磨後,很長時間身上還到處是大塊的紫斑。惡徒們經常在深夜對大法弟子施酷刑。我在監控那裏發現劉志英替我寫的保證書撕掉了。
不久我被調到3大隊,同修們見我全身是傷,兩臂繩痕的傷溝很深往外滲黃水,兩腳大趾甲也脫落了,都為我難過。邪惡之徒和猶大們不讓堅修大法的弟子睡覺、精神摧殘、酷刑洗腦。鑑於這種情況,我和一部份同修們絕食反迫害,要求「還師父清白」,「還大法清白」,「釋放所有被非法關押的大法弟子」。這期間我和另兩位同修被調到304中隊。我發現原來表現很堅定的學員到這裏很快被所謂「轉化」和邪悟,懷疑食物中被放了東西,我更要堅持繼續絕食。惡警們拿雞蛋、小餅乾、西瓜等想讓我吃,看我還不屈服,張隊長給我上「斜拉銬」(即一手在斜上方,一手在斜下方,兩腳站立方向不一致,且一隻腳只能剛著地)時間稍長,鬧心難過,兩腳不住的動來動去,本能的想依此得以緩解,鞋掉了也穿不上,光著腳掙扎著。原來開著風扇,上銬就關上了,汗就可想而知。我體會到「欲生不能,欲死不得」這句話的真實含義了。精緻的食品、雞蛋就在眼前窗台擺著,我熬過了一天零大半夜,早飯前鬆開手銬。張、王兩隊長叫我去吃飯,我不吃,就用電棍把我電倒在地上反銬雙手,用竹片往我嘴裏塞毛巾。電擊皮肉冒出的是煙還是熱氣分不清了,發出的氣味難聞極了,我痛苦的打著滾、掙扎著。10分鐘後,拽掉毛巾,他們一個拿著饅頭,一個拿著電棍,湊到嘴跟前,逼問吃不吃;「吃了就沒事,不吃還電!」又把我雙手左右分開銬上,猶大們圍著。屢遭酷刑,身體越來越不行,上廁所都需要人架著,直到現在,路走多了腿就跛。
我受刑期間,家中兩次來人看我不叫接見。2002年1月,丈夫死於非命,村幹部和鄰居經縣公安局到勞教所要求准許我請假回家辦理喪事(屍體在家停了20多天)。回家後我才知道家裏發生的一切。村裏的鄉親們說勞教所大隊長散布謊言說:劉素香不回去,不見村幹部,不要家了。我回家幾天後,回娘家看望老母親,大弟弟剛和我說了幾句話的功夫,崔廟鎮政法委書記李玉良(新任)指使3惡徒闖入我家,阜城縣公安局來了20多個惡警把我母親打倒在地起不來,弟弟被他們扭著胳膊,兩個人抓著頭髮,打著、踢著弄上汽車;老母親被4個惡徒抬著胳膊、腿(仰面,頭向後耷拉著,情景很慘),扔在車裏。副局長寇文通,惡警張志軍讓母親看著把弟弟綁架到椅子上打,母親看著弟弟,弟弟看著母親。弟弟被打昏死過去。2002年2月22日堅定的大法弟子,我的弟弟劉秋生被迫害致死。
在以後的日子裏,鎮政府的惡徒們逢年過節、「敏感日」或中共有甚麼會議,總少不了來騷擾。
崔廟鎮黨委書記劉新榮電話:0318─4623359(宅電)、0318─4828462(辦公室)、手機:1393182428,13803188089
崔廟鎮法委書記李玉良:先後有三個手機:13131836243、13785830619、13013276207.家宅電話:0318─4715370,4728637
原崔廟鎮政法委書記曲東武
通訊地址:河北省衡水市阜城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