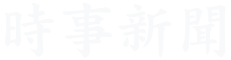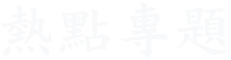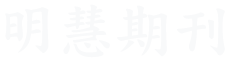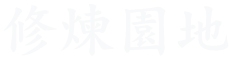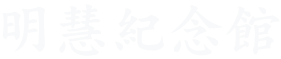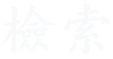山西太原老年法輪功學員自述幾年來遭受的迫害
我家住山西太原重機(重型機械集團公司),今年56歲,煉功7年了,當時因為身體不好,才走上修煉的路。99年7月20日,驚聞有幾個煉功點輔導員被抓。我們都是在做好人,又沒有犯法,憲法規定公民有信仰自由,怎麼抓人呢?於是就去了省委要求給個說法,並要求放人。
政府裏好久沒有人問一下這些老百姓來這裏幹甚麼,而下午來了好多武警、幹警,不容說話,連打帶拽往汽車裏推。那天正下雨,好多人被弄的一身泥。我們是煉功人,我們在哪裏都是好人,大家都靜靜的等在那裏,把周圍的環境清理的乾乾淨淨,自覺的沒有影響任何交通。公安人員戒嚴不准路人通行,反而在電視中說我們阻礙交通。
緊接著又被打成「非法組織」,心裏更不理解了。於是2000年6月初我一人去了北京信訪辦。當時信訪辦外面全是全國各地的警察、便衣、警車,問我是那來的,我說是太原的。當時正好太原的警察不在,沒有被抓起來。
進了信訪辦,剛填好表就沒有自由了。那裏的工作人員通知山西辦事處來帶人。辦事處通知當地派出所,派出所通知單位把我接回來。回來到當地,往派出所小黑屋一關就不管了。小黑屋只有一個2米左右的小凳,裏面臭哄哄的,吃飯、喝水無人過問,大小便得讓你去才能去。
2001年7月4日,片警趙小花和另一個幹警把我騙到派出所,說所長找我談我工資的事。因為我的工資已停發,所以就去了。就這樣把我關入了拘留所,非法拘留了50多天。當時所長是閆斌,副所長是莊漢斌。在拘留所50多天裏,沒有開水喝,夏天蚊子、蒼蠅特多,沒有熱水洗澡,連自來水都不是常有。號房裏關的人太多,床上睡不下,只能在地上睡。
在拘留所,不法人員毆打大法弟子那是常事。楊幹事、陳幹事等好幾個幹事打人、罵人是家常事,根本談不上人權。吃飯更是差,饅頭常是不熟的,菜裏常有蟲子,豆角根本不揀,拿刀一切便行,所有的菜都只煮一下放點生油。要是抓住大法弟子煉功,輕的罵、重的打,盤腿也不允許,見了就罵。不去那拘留所真是不知道那裏的黑暗情況。電視裏整天說別國如何如何不尊重人權,在中國連人權也沒有。
2001年12月4日,我去派出所交照片又回不了家了。於麗麗讓我等片警趙小花,不讓我回家,晚上被於麗麗送入拘留所。在拘留所一關又是50多天。大法弟子開始絕食抗議,在絕食期間聽一個香港經濟犯說,你們快吃飯吧,部隊帶著槍來了。
在這兩次拘留期間,我們和犯人都在裏面給幹警幹活,有幹私活的,有幹公活的。私活是給幹警做衣服,公活是做防電膠鞋和撿豆子。當時騙犯人說是幹點活給改善伙食。我兩次拘留期間被勒索交了6000到7000元,全無收據。
2002年,在街道書記和主任的合謀下,派出所又將我騙到了洗腦班,當時是片警趙小花和另兩個幹警把我劫持走的。
洗腦班裏的那些幹警手段更邪惡。因我被早早的關了禁閉,外面的情況了解不多。在小屋裏面,兩個人吃喝拉撒全在房間裏,沒有自由,飯給一點,每頓飯給很少,有一個年青的同修根本吃不飽,我和另一個同修省下來給她吃。吃飯錢我們自己付。冬天很冷,我們睡在沒有暖氣、沒有太陽的屋子,被子又薄,向幹警要,她們根本就不給。
那一年冬天零下22度,洗腦班不法人員逼迫修煉人一站一上午,連近70歲的老人也不放過。幹警崔瑩、李富娥成天整大家、罵大家,只要一睜眼就開始整人、罵人,反正是個罵。最後連做飯的炊事員也看不下去了。
一開始洗腦班裏來了一些街道的工作人員和幹警,他們中一些有良知、有善心的人看到了洗腦班中的真實情況,紛紛離開那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