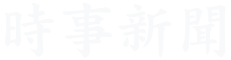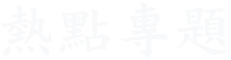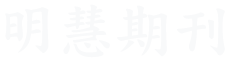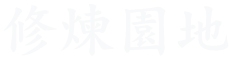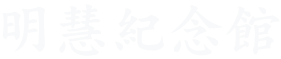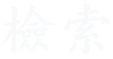掙破情的束縛 跟上正法進程
兒子倆口受惡黨謊言毒害,對我修大法有誤解,認為「政府不讓練就別練了,再練就是自私、不顧別人。」初進兒子家門(不在一城市住)兒媳曾趕我走,剛出生的小孫子不要我抱,怕像惡黨謊言中宣傳的那樣把人「掐死」;削了水果時怕我手中的刀子飛到她身上,做好飯不吃,怕……,甚至給他們買的保健品都不用。兒子雖知大法好,但沒深入學,有懷疑。
這些我全不放在心上,依然做一個母親、一個大法弟子該做的,我堅信按法理去做會盪去她心中的陰雲,啟迪她的善心,破除她的誤解。因此,我沒有煩惱和憂愁,做著一應的家庭瑣事,晚上學法輪功,寫信講真相。漸漸的兒子明白了,兒媳也露出了笑容,和她姪女說:「你奶奶太善良了。」孩子也給我帶了,換季時主動給我買衣服,提醒我發正念,勸她親友三退。
看到兒子家的變化,我自以為把他們「圓容」好了,漸漸的起了歡喜心。放鬆了做三件事,被求安逸心所帶動,學法少了,而且學法發正念犯睏,信也不寫了,幾乎不出門勸三退,認為人生地不熟不好開口。
不知從甚麼時候開始,兒媳也不提醒發正念了,而且一聽我們提惡黨(老伴是同修)就反感,我們揭露迫害,她說我們成了「祥林嫂」。我奇怪為甚麼出現了「反彈」現象。我越發的多幹活,多照顧以感化他們,把老倆口的退休金幾乎都貼在了生活上。新做的飯菜放在他們面前,我們吃剩的。剛洗完衣服又扔過來幾件,那我就洗完了衣服再學法,等等。只是順從,沒有意識到是另外空間的邪魔鑽了空子。不讓提惡黨就不當她面提了,無形中承認了舊勢力,還覺得無怨無悔帶工資的保姆哪裏找。
終於一天,兒媳說:「我們不需要保姆,而是一個能給我們出主意的媽。」我當時也忍不住回了一句:「是大法改變了我的心,否則我一個堂堂的××師為甚麼會低三下四的伺候你們?」這句常人不如的話引來了她的一頓連珠炮,忘了大法弟子的一思一念都得在法上,否則會使他們得不了度。最後他們倆口以照顧我為名,不讓在她家待了。
我真得好好找找自己,我是站在法的基點上把他(她)們當作眾生慈悲救度了嗎?不是,而是常人心佔了上。因為渴望救度的生命不要「保姆」,而要一個從新給他們生命的「媽」。
用常人的手段,其實就是「情」,我不就是做「過」了又產生新的執著了嗎?怕他們不明真相,有機會就說,導致「煩」。電視報導的「天災人禍」,不管理解不理解,以一種「警示」的口吻去評論,使他們說我們「幸災樂禍」。(修煉人修口沒做好)。看他們狠勁摁著小孫子「灌藥」,孩子拼命哭喊,我就揪心,一概的順從、承受不去說,還認為他們在給我創造提高心性的機會。同修給我指出這是沒做到真,沒做到善,只為了自己「提高心性」讓別人去造業。講真相中碰到不好講的會認為這是「救不了的那一半」。勸三退覺得人生地不熟,最可怕的是覺得師父說付出多少得到多少,認為我付出的少就少得點也比掉下去的強,其實這顆心已經掉下去了。三件事也做,但是不緊不慢,其根子是怕「落下」,又是多強的執著。兒子家不想讓我在那兒,我悟到是師父點化我回到我該去的地方發揮大法弟子的作用。
回到我的居住地,靜下心來學法,從新背《正法時期大法弟子》、《路》,明白了正法時期大法弟子一定要跟上正法進程,除了自己修煉之外,最大的責任就是要救度眾生。我的生命是大法延續來的,一定要百分之百的溶入正法洪流中,不能陷在家庭小圈子裏。真的是時間不等人,正法洪勢一過,一切結束,那時甚麼也來不及了。想起三年前做的一個夢如今歷歷在目:在過一條大河時,河水已沒過橋面,我在橋上淌著水前行。行至橋中,發現橋北側一些人在河裏游泳,而橋南側連天的大浪像一座大山壓下來,我一邊向對岸狂奔一邊呼喊河裏的人快上來,可是聲音被滔聲淹沒,等我跑到岸上,再看河裏的人已無影無蹤。這是師父在點化我要抓緊救度。大法弟子是眾生得救的唯一希望,我不能因自己的懈怠,而看著眾生被謊言矇蔽而毀掉。
通過學法歸正了自己找到了自我。我要跳出這個情,修出慈悲。現在我們把時間安排的緊緊的,以前幾個月沒勸退幾個,現在不長時間就勸退八、九十人。這還遠遠不夠,要向精進的同修學習,更多的救度世人。最後重溫師尊在《洛杉磯市講法》「希望大家在最後越做越好,千萬不要懈怠,千萬不要放鬆,千萬不要麻木」。層次所限,望同修慈悲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