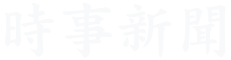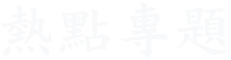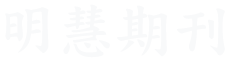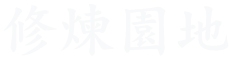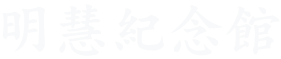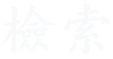倉鼠日記(1)
【作者聲明:】這是完全根據親身經歷記錄的非文學作品。我的寫作是獨立的,我現在沒有網絡、沒有朋友、沒有任何接觸的人,任何人都不應受到株連。因為本文純粹屬歷史記錄,無所謂作品版權,故任何轉載都無需徵得作者同意。但應該注意的是:所轉載內容必須完整統一,與本文相同,不可隨意篡改、斷章取義或有意誤導。(2009年6月30日)
2008年9月16日
號裏太冷了,實在受不了,大家都把身子蜷起來,縮在僅有的衣服裏。我對自己身體的感覺已經變得麻木,只知道自己還活著,其它問題也顧不上了。
這段時間,嚴管組對我的「照顧」依舊。我極少睡覺,每天都被無數次踢醒。我已經暈過去了幾次,腦袋摔到了地板上,很疼,也很舒服。幾天前,我還在發高燒,渾身發熱,我要了一瓶子水,喝下去,挺了過來。
榮升到市所
還沒到吃早飯的時間,那位可愛的辦案警察又來提我。跟他一起來的是一位老警官,外形似地缸(東北農村腌醬的陶器)。按照規定,押解犯人至少要兩個警察以上。按照潛規則,犯人家屬在這個關口上都要打點一下,那樣犯人和家屬就可以單獨相處,甚至可以在酒店聚餐一頓。
我是個例外的特殊情況,他們這麼早行動,就是為了避開我母親(一名法輪功學員)。但是母親隨後還是找到了我,應該說沒有母親的堅持,可能就已經沒有了我的生命。
這麼長時間了,終於再次見到了陽光,隔著車窗玻璃,眼睛被刺得睜不開,那種感覺就像剛剛來到人間。
「怎麼這麼瘦了!」警察見到我的第一眼,吃驚地叫出聲來。見到他,我感到很親切,這麼漫長的時間裏,唯有他始終在「陪伴」我。
路上,老警官問:「法輪功啊?」辦案警察答:「信神的,送精神病院。」一路上,我就不停地瞅外面,我對這條道比較熟悉,肯定不是朝精神病院方向。
車子一直開到市郊的市看守所的大門口。高牆外,滿坑滿谷的,都是人。奧運會把商家搞得一片蕭條,就這裏生意興旺。
在門廳裏辦手續很繁瑣,管事的警察牛X得不得了,但是令我奇怪的是,沒看到一個人穿警服。終於辦理完畢,蹲的時間長了,我掙扎著站起來,走廊裏一個女人尖利的聲音在喊我,我答應著。「怎麼不早點送來,讓我等,他就是某某某嗎?」檢察院負責送函的女人進來,拿著一頁《委託辯護人通知書》,問我是否請律師。
我想了一下,說:「我要請律師。」我知道我不會得到共產黨的公正審判的。以前我也打過官司,是向人討債,當時的法官和律師都非常貪婪,根本無視我們平頭百姓的利益,何況我的案子涉及共產黨,全部事宜都由它一手決定,我請再大的律師也沒用,豈不是白送錢嗎。
我留下家人的名字和電話。她氣哼哼地責怪我,在座的幾位警官都上來關心她。我把紙遞給她,還想說幾句話,她連看也沒看我一眼,扭扭搭搭走了。警察們一直不讓我找律師,她只要能夠通知到我家人,讓他們知道我現在的位置,我的生命就安全了。
體檢不合格
經過武警把守的鐵門,進入高牆內,在空空的大樓裏,我們上到了二樓,在角落裏找到醫務所,裏面除了幾個人在打情罵俏,甚麼醫療儀器都沒有。那個女人在通電話,內容是給人擺平事。好像事情不太好辦,錢還沒到位,她撅著嘴。
等了許久,一位老大夫回來,他給我檢查心音,邊測邊問:「自己感覺怎麼樣?」「可以吧?」我滿不在乎。「我們不能收他,已經這樣了,死在這裏怎麼辦!」我第一次聽說我得病的消息。我從來沒想過這件事。我一直認為只要意志堅強,疾病是不會戰勝我的。
「他有啥毛病啊,身體好著呢!」送我來的警察應付著。
「不行啊,心臟不行了,看他那臉色,就知道了。」
「他不一樣,你們不收,我們沒法處理。」警察無可奈何地解釋。
一般情況下,國保的權力都大於其它部門的警察。不過,這次是求著他們辦事,關係顛倒了。
老大夫看了一眼罪名標識牌,又端詳了一下我,搖搖頭:「不行,這個絕對不行,沒有證明,我不敢收!」
下樓的時候,兩個警察都忿忿不平,莫名地發脾氣:「*媽的,讓他在裏面呆兩個月試試,他會是甚麼臉色!」「就他這*樣的還得病,咋不嘎嘣一下死了呢!」
老警察對我懷恨在心。我滿腦子疑問:「怎麼得的心臟病?」他們的牢騷沒灌進耳朵裏。
上了麵包車,車子向市區方向駛去,「我們是去哪啊?」我心裏嘀咕:不會把我再送回去吧……
「某某某把嘴閉上,不然給你上大鐐!」老警官一路上都黑著臉,罵罵咧咧的。
辦案警察一臉的壞笑,他比老警察還急呢:「我剛從阿城(附屬的一個縣級市)趕回來,我們正在那蹲點呢,就是為了他,不送不行了,怕死在區所。」殊不知,區看守所和區公安局本是一家,辦案警察還是比較有事業心的。「媽了個*的,中午跟人約好了打麻將,現在回不去了。」我想打麻將是假,沒得到實惠是真,醉翁之意不在酒啊。
醫院做「特診」
車子一路疾駛,衝向公安醫院。
我戴著手銬,跟在他們後面。樓上樓下一通找,心臟明顯受不了了。辦案警察怕我檢查過不去,讓我蹲到走廊的牆角。大概公安醫院也對外,看病的人熙熙攘攘的很多。辦案警察遇到老同事很興奮,海闊天空地聊,從一個人聊到另一個。
前後進來幾個大夫,最後說必須搞「特檢」才行。他們在我那張表上蓋戳,每次都把我叫過去在戳的下面按手指印。我的手指是不可以用了,連管教都說不行。我離開區所辦手續時,要我的手指按機器上的識別器,自動刪掉我的記錄,但是反複試了幾次都不行,管教說我的手指(指紋)模糊了,最後不了了之。
我又被帶到後樓的二層。在心電室,兩名女護士給我做心電。我躺到床上,露出上身和腳脖子。她很快速地粘了幾根線上去。
我身上癤子和被打的痕跡很多,皮膚基本上不是人色。女護士嗲嗲地說:「心顫、早搏、心律不齊,夠全的了。」警察在她耳邊講著笑話,發出一陣陣的笑聲。「咋的,還不起來,想在這吃中午飯啊,你有錢嗎!」辦案警察打斷了我的沉思,手裏的特診收據在我眼前揮了一下,我明白在我存款裏又少了200元。
辦案警察讓老警官帶著我先走,護士小姐在那邊認真地鼓搗那幾張紙。當我在麵包車裏快被蒸熟的時候,他一臉輕鬆地回來,「搞定了」,快速發動了車子。果真,當那張紙放到所長面前時,我被馬上放行。
市所301監值班的警官威風凜凜地坐在那裏,問我:「你怎麼甚麼都沒帶來,你怎麼生活啊!」我不知道怎麼回答他,從區所出來甚麼都不許帶。我懇求辦案警察給我留點錢,他給管教200元,說是買套被褥和必要的牙具。辦案警察背著我向他交代事項。我也很發愁,只有可能判死刑的才到這裏,我需要做長期的準備。
辦案警察走了,從此我的命運交到了這幫管教和警察的手裏。
路過天堂口
值班的警官高大威猛,那件特大號的警服也沒能蓋住他的肚子。他「吭吭」著鼻子:「沒有我,你在這裏怎麼活?我的心眼好,我一看就知道裏面有事,愣給你扣下了這點錢,你懂不懂?」「我懂,但是我真的沒有別的東西孝敬您了。」我被他的陰陽怪氣弄得無所適從──現在我一無所有,連身上的衣服都禁不起秋風的侵擾。
「你不許跟他們說話,只能老老實實,不許亂說亂動。」他繼續拿話敲打我,並且了解了我家裏的情況。我想:他怎麼還不把我送進去?警察們聊以為生的,只是身上那件衣服;脫了衣服,他們禽獸不如。還沒進到號子,我心裏已經有了很重的陰影。
我的腳邁進監房時,已經是下午三點了,我一整天沒吃沒喝,有些虛脫。
進來後,被喝令蹲下,脫光了衣服,接受嚴格細緻地檢查。最後,他把頭甩了一下,說:「過去,跟坐班彙報。」
「甚麼事進來的?」坐班把臉側過來,他正在睡午覺,伺候人跑過去,扶著他半坐起來。
「煽動顛覆罪」
「*的,還有這種罪!」我心裏有點自豪──我是這裏唯一的政治犯。
藉這個機會,我的眼睛在監室內巡視了一圈。昏暗的房間中央是一條很窄的過道,兩側是東北式的通鋪,牆上貼著「嚴打」的布告。五六個拖著腳鐐子走來走去的人,各種顏色的衣服和被子。有人披著衣服,有人光著膀子。「嘩楞嘩楞」的腳鐐聲迴盪在整個樓道裏,亂七八糟的,像是從幾十年前跨時空而來,充滿了一股陰森森的氣息。
「這是甚麼地方,知道嗎?」
「鴨子圈。」最早的一個同事住在附近,所以我知道這個老名字。
「這是三大刑的地方,進來的別想出去。三大刑知道嗎:死刑、死緩、無期!」
「我不可能有那麼重啊。」
「*的,沒那麼重,來這裏幹嘛!」
「不是我要來的,是他們拉我來的,我也沒辦法啊。」
「是不是很長時間沒洗澡了?」
「是。」
「給他洗個澡!」
他們真的沒客氣,一起上來十幾個犯人。兩個人一組輪流向我潑水。一盆接一盆的涼水從頭淌至腳。這裏的水和家裏的水不同,好像全是井水,涼得透骨、冰得刺骨。他們用這種涼水洗臉之前,都要在水盆裏攪動一會,等涼氣散一下再用。
我在痛苦中掙扎、顫慄。一直到我臉色發青、四肢動彈不了,他們才罷手。
一個管教拿著相機過來。伺候槽子的兩位沒等我反應過來,就快速地把我按坐到炕鋪的前頭,讓我自己在小板子上寫名字,雙手舉起,在我背後展開一張布,上面印有標尺,照我報的身高數值。他倆上下調整了一下位置,尼康相機的鏡頭伸過欄杆閃了一下。我的照片掛到管教走的監道一側,下面標上所犯的「罪行」。
「文字獄」裏的錦衣衛
301囚室外過來一幫警察,他們橫衝直撞,個個兇神惡煞一般,黑壓壓的像一群黑社會,為首的領導被前呼後擁著。號裏一陣忙亂,大家趕緊各就各位。站在中間的那人很兇,肯定是一把手,我也弄不清楚是所長還是支隊長。其中一個隨從指著我:「就是這小子!」他瞄了我一眼,咧開、油乎乎地嘴裏擠出一句:「是他*的跟人不一樣啊!」
其他人都向我投來奇異的目光。看守所很少有上級巡視,有也是一幫男男女女趾高氣昂地在監道裏走一圈,都不會往號裏看一眼。他們這趟是專為我而來。坐班被找出去開會,布置對我「管理」的任務。
不長時間,坐班就回來了,他說我身上有蝨子。我說不可能吧,我從來沒長過蝨子。「他*的還敢跟坐班犟!」他拿著噴霧器向我身上噴。我一躲閃,他的拳頭就劈來,我渾身濕漉漉的,難聞的敵敵畏嗆得我睜不開眼睛。坐班狂笑著,好像中了大獎。那個噴霧器是向負責噴藥的老頭借的,那人每天對監道噴一次「來蘇水」。他背著噴霧器經過的時候,滿屋的犯人都捂鼻子。
這個號子的坐班叫賈坤,過去是個警察。賈坤吸毒,同案都是警察。後來我見過幾個,也都吸毒。我呆過的三個號子,販毒犯和吸毒犯都不少。坐班都吸毒。在勞動班,坐班帶領七八個人蹲在一起吸食毒品,吸完了兩眼發光地聊天,整整聊了一宿。我白天還有很多活要幹,把我攪得心煩意亂,不過那次我算是開了回眼界。
吸毒是高收入人群或者上流社會的活動,像警察和小偷都屬於其中。黃賭毒的市場運作需要政府和軍警的協調,所以在犯人中,他們的地位最高,最受人尊敬。號裏第二號人物慶哥也是毒販。慶哥在江湖裏混了多年,長得非常像《少林寺》裏的禿鷹。他是賈坤的軍師,有文化、有思想、心狠手辣。
在賈坤的一手安排下,犯人們組成了以「禿鷹」為主的幫教組,對我實行肉體折磨。全體人員都被發動起來,我的到來改變了整個監室的「面貌」。幫教組的邪惡來自共產黨播在其體內的毒種,凡是正義的東西在它周圍出現,它就感到自身受到威脅。
當晚,我的被褥和洗漱用品沒有送來。我以為需要等到明天,可這一等就等了半個月。這中間,我沒有洗過臉,也沒有睡過一宿覺。管鋪的扔給我一片破棉絮,上面滿是污物和血跡,這就算是我的被子。301房間處於前樓的拐角處平時就陰冷潮濕,那幾天他們特意開著窗子,因為他們都有棉被,完全可以抵禦這個季節的風,只有我一個光溜溜的,甚麼也沒有。
躺在冰冷的鋪板上,晚上睡覺的時候,心臟跳得非常厲害,「噗嗵噗嗵」的。斷斷續續的昏迷。漫漫無盡的黑夜在一點一點地吸走了我的熱量,我不敢睡著,怕自己被凍死。有一段時間我的神智模糊,感覺不到自己的存在。這個時刻,我才知道,我是怕死的。
等我醒來的時候,天快要亮了,我眷戀的生命還在,它沒有被死神帶走。我下定決心,一定要挺住,不能死在監房裏。以後的每一晚上,我都面對著可怕的和寒冷徹骨的長夜。
2008年9月17日
太陽起了老高,號裏才有了光亮。
「小子,把褲子脫了,讓我幹一下,政府同意讓我舒服一下。」一張猙獰的臉靠過來,我向後退縮,嘴裏磕磕巴巴地應付著:「我跟你商量點事,我們先說說話。」
他開始扒我衣服。我非常緊張,幾乎大叫起來。大家都往我這邊靠,十幾雙眼睛一起盯著我。這個叫「大傻」的死刑犯突然哈哈地大笑,用手銬砸我的頭,問我疼不疼。我搖頭苦笑。他繼續發瘋,用鞋抽我的臉,我的眼睛腫了起來。
賈坤讓幾個罪小的犯人打我,他們猶猶豫豫沒動。幾個死刑犯被單獨找出去訓話,回來後你一言我一語地分析我,大概是說我為了出名作秀,目地不純啊;為了發洩私憤,於國不忠啊之類的。
「*的,我一看到他這種人就來氣!」
「怎麼出了你這麼個怪胎!」大家不溫不火地發著感慨,此時的「大傻」露出少有的笑容,好像做了一件得民心的大好事。
幫教組成員要夜裏給我上「小班」,白天給我上「大課」,所以他們白天可以跟著值夜班的人一起睡覺。過去有三個鋪位不疊被,現在特意為幫教組增加了一個。
這些犯人平時沒有娛樂活動,把迫害我的事當成看演出。
最後的勝利者
我向茅坑方向挪動,趁人不備出溜到地上。我大便已經憋了兩天,肚子裏實在受不了,快要拉到褲子裏了。
「這麼多人還看不住他一個!」禿鷹向他們嚷著。一個伺候槽子的薅著我脖子把我拖回去:「等到我幹完活,你再下地,知道嗎!這是規矩,你以為在家呢!」
「那你甚麼時候幹完活啊?」
「我忙完了通知你。」
「大哥,都兩天了,你還沒忙完啊!」我都要哭出來了。
「你一點都沒改造好。」他對我的表現很不滿意。
我一週才有大便一次的機會,但是他們不讓我上,也不讓我接水喝。我一動他們就打我,這麼多眼睛看著,根本不能有一點自由。我在痛苦地掙扎,旁邊的犯人厭惡地罵著:「這麼臭啊,他拉出來了!」賈坤:「趕緊讓他上。」
我抱著肚子到茅坑。兩隻大桶在裏面,桶裏是為槽子洗澡準備的滾燙的開水。我沒有地方啊,只好側著身子擠進去,基本上抱著水桶。「媽的,拉到外邊了!」這傢伙在找茬,賈坤磕巴也沒打地說:「讓他吃了!」幾個人上來把我往便器裏按,「給共產黨磕頭、磕頭!」
頭一點點靠近,終於看清了上面的屎,我只得用手拉到裏面。那幾個人哈哈大笑:「你不知道髒啊,他是個瘋子,哈哈哈……」我的頭「梆」的磕到地上。
打我的人姓張,年齡26歲,後來我們成了朋友。我叫他「教獸」,不是因為他學問高,他只有初中文化。在我面前,他以其卓越的「自然知識」藐視我。他在戲弄我:「你說甚麼?」拿個小盆舀了熱水,往我身上潑。我的手和後背都被燙禿嚕皮了。
他們是勝利者,他們的人性已經死去了,勝利者通常最先死去。
獄裏的法西斯暴行
我的心臟跳得厲害,全身突突,腰也直不起來。我說我的心臟不好,做了特檢才進來的。他們誰都不信,「心臟不好,管教能讓我們打你嗎!」
「把他褲子脫了!」監裏最暴躁的死刑犯「大成」一躍而起,上來幾個小子從下面把我褲子往下拽,上面有幾個人按著。「大成」揮起棍子掄圓抽我的屁股,1、2……30、31,我在心裏數著,咽了一口血,咸乎乎的,神經已經麻木了。號裏的五六根棍子都被打廢了,放開我的時候,屁股已皮開肉綻、血肉模糊,我再也無法坐著。
後來他們就自己動手做棍子。先用報紙搓一個實心的芯,一層一層地用力卷,外面再卷一層刷了糨糊的布,等乾透了再卷報紙,最外邊用膠布粘好,在兩端套上帽,最後做好的棒子和木質一樣的強度。
這樣的棍子也很快打折了,我身上到處都是一道道的血檁子,整個身上都是紅紫色的,而且讓我品嘗了許多種徒手的方式。綜合比較來看,徒手比使用器械要乾淨利索。號裏準備有縫東西的針線,針是縫麻袋用的大針。他們就用那個針扎我的後背、膀子和手指。我疼得昏了過去。
打我的犯人叫高殿成,身體素質非常好,戴著手銬腳鐐還可以翻跟頭,大家都叫他「大成」。「大成」是古鐵市場蹬三輪拉腳的。號裏做桃核工藝品,他負責管理錐子一類的工具。他的額頭有兩個對稱的突起,腦袋的形狀像個六稜錐。
每次,他都拖著沉重的鐵鐐,沖到我跟前,明晃晃地用錐子捅我眼睛,只要有一次我躲閃不及,眼球就會被扎爆,這實在是非常恐怖的場景。現在想起來都心驚肉跳,多虧他戴著鐐子動作受阻,我又幸運地快速躲閃開了,只是太陽穴旁邊被捅過幾次。
幾天以後,我身上被扎的小孔,不下幾千個,我的臉上也被劃了多個口子,全身上下血痕累累,有的地方腫起來,嚴重的傷口已經感染。警察用手槍對準我腦袋的那一瞬間,我都沒這麼恐懼。我常常想,如果當時那只黑洞洞的槍口裏真的射出子彈,我也不用遭這麼大的罪。人生在世,白駒過隙,不知何事縈懷抱。
棍刑、錐扎都讓痛苦延續太長,所有器械的方式遠遠不如徒手。我被按趴在鋪板上,一個人坐到我背上,反著提起我的胳膊,做划槳的動作,我在下邊痛苦地蠕動,身體就不自覺地向前一點點挪。在我的後面還有一個人,把他的拳頭放在我的膝窩裏,另一隻手使勁壓我的腳腕。我在下面極度痛苦,幾乎喊不出來聲。
我開始逐次體驗「划船」、「推牌九」、「吊爐餅」等各種刑罰。我清楚地聽到自己的骨頭「喀嚓喀嚓的響聲」。我的後背被一條腿頂住,沒法動,疼痛讓我陷入昏迷。他們也被累得滿頭是汗,不停地換人。我的膝蓋是酸軟的,想站都站不住。他們揪著我的頭髮,拖著我往我下身踢,一會就滲出了血。我知道我會在這部巨型機器裏被漫不經心地絞死,我開始服軟,求他們放過我,他們看著我,癡癡地笑。
他們放開了我,我的腿還在抖。我的腦子裏卻在想,滿清十大酷刑可能不是真的有,那些複雜的器械是不必要的,最有效的方式肯定是人的兩隻手。中國的監獄一直以來就是共產黨暴力最猖獗的地方,用塑料管打人,用打火機烤熟指甲,一會就「啪」的一聲裂開、向上翻起。共產黨禍害人的創意總是出類拔萃。
中國的教育不是為了健全公民的人格,接受它的教育就是吸食共產主義精神鴉片,會無中生有地產生出仇恨來。所以中國沒有教育,只有「教導」,教導人民戴著有色眼鏡看待世界。尊重每個人的獨立性,每個人是獨立的個體,才能構成相互尊重相互平等的多元社會。
這裏的夜晚不平靜
臨近傍晚,「610」過來一趟,在窗口外斜眼瞅了一眼,走開了,他像個時遠時近的幽靈。
幫教組的人一到晚上格外興奮,當別人進入了夢鄉,我還被迫光著腳,蹲在鋪板邊緣的角鐵上。我睏得不行,歪歪扭扭地站不穩了。
賈坤讓金剛拿來一個豆奶的瓶子給我喝。我確實渴極了,但是,從他們怪異的表情判斷,這是一個愚弄人的陷阱。
我堅持不喝,兩個夜班上來堵住我的嘴,勒住我的咽喉,強行讓我下跪。他們的兩雙手把著我,拳頭不斷落到我頭上,我就用胳膊抵擋著。當他們已經停下來的時候,我的手還在不自覺地擋。我開始感到絕望。
熬到了後半夜,賈坤已經睡完一覺醒來,再次把我叫過去。我的腿一瘸一拐的,我說,要不我們都退了一步,我可以按你們的意思吃辣根,用吃辣根代替喝「豆奶」。他也痛快地答應了,另外再加一碗辣椒水,就著熱水喝。
我一狠心,就這麼地吧,豁出去,反正自己都這樣了。在小鋪出售的商品名單裏沒有辣根,這是610專門為我準備的,我是逃不出這一關的。
剛咬牙喝下,「金剛」就把整管的辣根灌到我鼻孔裏。我張著嘴裏大口呼氣,他又灌了我一嘴。我被辣得鼻涕眼淚迸流,整個人往上蹦。他們呵斥我,不許跳!樓下睡覺呢!
「金剛」人高體壯,身高一米八五,體重超過二百斤,壓在我身上。幾乎是沒氣了,我還在捯氣,兩個夜班,「四指」和「長龍」又過來,把我推到茅廁,叫我「搗管」。他們把「自慰」稱為「搗管」。
我上氣不接下氣,一直抱著頭,一聲不吭,因為已經沒力氣了。這兩個小子,用粘著大醬的小木棍往我屁股裏捅,把鼻涕往我身上甩。我躲閃著,但力氣已光,掙扎不過他們,就這樣,他們一宿不斷地折騰我。
2008年9月18日
昨晚,我一閉上眼睛,「四指」和「長龍」就用錐子扎我腳心。
當我是法輪功
早上,他們兩個向賈坤彙報成果,賈坤問我:「他們用甚麼扎你?」
我答:「用的是錐子。」
賈坤:「我們監裏哪有錐子!」
我答:「那就是錐子類的銳器。」
賈坤咬著牙:「我讓你胡說!」接著過來提起我,像提著一隻小雞般扔到後門。我的身體虛弱得很,無力反抗。
他們把我手插到後門的鐵柱縫隙裏。賈坤掄圓了拳頭,轉身,朝我胸口用力悶。賈坤足有一百八十多斤,體格和泰森一樣壯,拳頭如小沙包一樣大。我在被連續的巨大的外力擊打,昏死過去……
醒來的時候,我還躺在冰冷的水泥地上。嘴裏鹹鹹的,咳嗽得很厲害。我試圖爬起來,胸口很痛,我懷疑是肺部毛細血管破裂。
我艱難地對賈坤說:「我有心臟病的。」
賈坤很有把握:「*的,還敢騙我!我都看過你的病例了!」
「我真的有病,你不能再打了,要出人命的。」我後悔不該體檢,這不成打死我的誘因了嗎!
「你不是法輪功嗎?怎麼不忍了?」「長龍」最能煽風點火,關鍵時刻總少不了他。
「誰說我是法輪功?我不是!」我一而再、再而三地聲明這事,還是把我當法輪功打,我被氣得直哆嗦。
「不是法輪功怎麼反社會,我怎麼能相信你?」
「你問問警察,他們都知道,法輪功是說真話的,說自己不是的那就肯定不是,這還用證明嗎?」我轉頭看賈坤,他點點頭,表示我說的話對。
我又加了一句:「不管是不是法輪功,你們都不應該打,難道法輪功不是國家公民嗎!」
「禿鷹」在一旁有滋有味地看了許久,這當口又來上一句:「就你這個熊樣,病病怏怏的,老實待著得了,反共產黨,你還反窖了呢!」
他們幾個人一起上,一人抓一隻胳膊,一人拖一條腿,一個人去扒我的褲子。我幾次甩掉前面的兩個,一次次他們又抓住我,用力掰我手指。
我把兩個人同時摔倒,他們在後面邊踢邊拖,直到把我拖到鋪上。我的上衣被撕爛,褲襠開了線,我的力氣用盡了。
「四指」用塑料瓶砸我的手指頭。「長龍」用鞋油抹了我滿臉黑。我痛苦地呻吟,他倆卻熱血膨脹。幾個人把我脫光了一頓暴踩,都累得動彈不得,他們才肯罷手。
這是他們對法輪功無數次暴力的延續。這是一場一個政府對一個公民的戰爭。戰爭的雙方,政府佔有了絕對的優勢,個人力量的渺小幾乎可以不計。但是,在精神的世界裏,政府是微不足道的,個人才是最強大的,個體的勝利是永恆的。
賈坤說,監控器照不到茅廁位置。我懷疑這是藉口,那種黑色的可以旋轉180度圓球,怎麼可能在這個不大的空間產生觀察死角?我在昏死的前一刻還在呼喊:「我的心臟不行了!」隔壁的警察看不到,還聽不到嗎?我每一次被廝打,管教都未出現;能夠挪動他們屁股的,唯有金錢和美女。
人的死亡方式有兩種,一種是肉體的消亡,一種是精神的消解,暴力消滅不了思想。我方感知法輪功在用個體的苦難喚醒民族的新生,他們以愛報恨、以德報怨是一種人類偉大的精神。
(待續)
(編後語:以上為王先生所記錄的自己被看守所關押期間的部份經歷,遺憾沒有完成。這篇文章是一位好心人偶然看到多年後,終於發給了明慧編輯部。據說王先生的父母幾年前過世了,他現在一個人生活,精神狀態不好,有時做臨工糊口,艱難度日。
從一九九九年七月至今,中共一直將「沒有迫害」作為洗腦所用的謊言之一。王先生的遭遇,反映了千千萬萬法輪功學員家屬的遭遇。他的文字,真實的記錄了當今中國社會的黑暗、殘暴、變態,也折射了中國大陸法輪功學員們所遭受的這場長達二十五年仍在持續的迫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