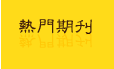電影文學劇本:送天行(三)
天安門廣場,天空布滿陰雲,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中,公安和武警隨處可見。
林心慧身穿一件鮮紅色的外衣,她向廣場中央走去,走到了人民英雄紀念碑北側,面對天安門城樓,她環視著廣場。
卿卿我我的年輕男女,奔跑打鬧的天真孩童,緩步而行的老人,成群的旅遊團體……執勤的警察、行為詭秘的便衣和停在廣場角落的警車。
林心慧看著越走越近的旅遊人群,她感覺自己是那麼高大,頂天立地,面前的一切都已從腦海中湮滅。她從內衣兜裏拿出了金黃色的橫幅,鎮定、偉岸地高高舉過頭頂,「真、善、忍」鎮懾著廣場上的邪惡,她用盡平生的氣力高聲呼喊:「法輪大法好!還法輪大法清白!法輪大法好!」
幾個警察衝過來,一個扯下橫幅,一個將林心慧打倒在地,用手撕扯著她的頭髮。
「法輪大法好!」林心慧依然奮力高喊著,警察一拳打在她的臉上,另一個用腳跺踩她的腿。警車閃著警燈開過來,林心慧被拖到警車上。
警車開動了,廣場上被震驚的人們透過車窗看到林心慧堅毅平和的面容,嘴角帶著鮮血,她依然在向廣場上的人們呼喊:「法輪大法好!」
(二十一)
看守所的審訊室裏,林心慧平靜地坐在椅子上,右邊眼眶處青紫,嘴角留有血痕。對面坐著負責審訊的科長聶京和記錄員。
「你叫甚麼名字?」
「……」
「甚麼單位的?」
「……」
「我問你是北京的還是外地來的?」
「北京的。」
「甚麼單位?」
「……」
「你有單位沒有?」
「我有單位,但是我不能告訴你。」
「為甚麼?」
林心慧(堂正地):「我曾經三次合法上訪,信任政府,我說出了我的真實姓名和所在單位,可是單位的領導因此而遭受了巨大的壓力,單位被通令批評,我也被停職,家裏的親人也跟著被恐嚇。我不願因為我合法的個人行為,再連累任何人,我對我自己的行為負責。」
聶京的臉上帶著嘲諷:「呵,合著你這是『四進宮了』?嘴茬子還挺硬的。看你這文縐縐的樣兒,你是個知識分子兒吧?不好好兒的做你的學問,跟著到天安門起甚麼哄啊?!」
林心慧:「政府錯誤鎮壓法輪功已經九個月了,修煉人被當作敵人,精神正常的人被送進精神病院,被抓捕關押的法輪功學員遭受各種非人折磨,甚至被迫害致死。現在法輪功學員只要上訪就被抓、被關、被毒打折磨,所有的正常上訪渠道成了迫害的開端,你是政府機構的官員,你說說法輪功學員能去哪兒申訴鳴冤?又能用甚麼樣的方式才能討回公道呢?!」
聶京(無賴地):「你甭跟我說這個!公道?甚麼是公道?政府說的就是公道!哪兒有那麼多說的?!」
林心慧:「我請教你一個案例可以嗎?」
聶京(喜形於色):「可以啊!我還真沒見識過哪個被審訊的人向我討教案例的呢。」
林心慧問:「你在回家的路上遭到土匪行搶,你為了自己的正當權利進行了適當的自衛,結果,土匪不僅搶走了你的錢財,還用刀把你砍傷。你報官申訴,卻遭到斥責。──第一,怪罪你自己不當心,專找土匪出沒的路走;第二,質問你為甚麼遭到搶劫還要反抗,你如果不掙扎老老實實地被搶,也就不會挨刀砍了。因此,你的申訴不予受理,你要是覺得不公,就再把你抓起來,整治你,直到你老老實實承認活該倒霉為止。你覺得這種邏輯合理嗎?」
聶京(像雞毛卡了嗓子眼兒):「這……,那……,不合理又怎麼樣?人家當的官,人家下的令兒,人家給我工錢養活我,人家指東,我就不能說西。如今人家命令整治法輪功,我也只能聽喝兒,抓一個整一個,要不怎麼叫『專政機構』呢!」
林心慧(正氣凜然地):「你說得不對,專政機關的職能應當是打擊和懲治壞的,同時呵護和保衛好的,專政機關決不應當把善良的人民作為敵人。你是個警察,你有你的職務,可你首先是個人,有血有肉,具有人的良知,如果為了執行命令而泯滅了你可貴的良心,那不是在幹壞事嗎?」
聶京(跳著腳兒地站起來):「嘿,是我審問你還是你審問我啊?幹我們這行的,良心沒有用。你也別說了,一句話,你到底姓甚名誰?哪個單位的?」
林心慧(冷靜地):「這個我已經告訴過你了,我不能再連累他人。」
聶京(瞪著眼):「這麼說,你不講了?」
沉默……
「那就對不起了。」聶京站起身走到審訊室門口大叫道:「大郭子,又一個死硬的,關起來!」
只見一個肥頭大耳的粗大刑警拎著手銬進來,他走到林心慧身邊:「細皮嫩肉的,何苦呢!」說著,給林心慧戴上了手銬,「到裏邊你就得後悔。走!」
林心慧平靜地站起身,走到門口,直面審訊官:「善惡有報是天理,你真的不為自己的未來著想嗎?」
「走走走!別廢話了!」叫大郭子的肥刑警推搡著林心慧走出審訊室。
聶京冷冷地看著一身正氣的林心慧被帶出審訊室,先是一臉的滿不在乎,忽然疑惑地瞪大眼睛,「嗯?天理?」
(二十二)
看守所所長辦公室裏,鄒所長正百無聊賴地喝著茶,翻看著當天的報紙,腳高高地翹到桌面上。
大郭子提著電棍垂頭喪氣的走進來,「所長,我可真是彈了,那個305真比石頭還硬。」說著一屁股癱坐在椅子上。
鄒所長放下報紙,「305是誰?」
大郭子面帶喪氣解釋著:「就是從天安門廣場抓來的那個女北京,給聶科長上政治課那個,她死活不說叫甚麼,編號305了。」
鄒所長把腳從桌面上拿下來,身子擰進了靠背椅:「大郭子,我可是第一次看見你服軟兒,你可是咱們所裏有名兒的『橫不過』,甭管誰到了你手裏都得是讓他說甚麼就說甚麼,今兒怎麼癟茄子了?」
大郭子粗著脖子解釋著:「我甚麼招兒都使了,吊銬、電棍、熬鷹、灌食……都沒用,她就楞給你來個一聲不吭。我就納了悶兒了,這煉法輪功的怎麼都這麼難對付,沒招兒能治得了他們。」
鄒所長:「怎麼,她還絕食?」
大郭子:「第四天了!不吃不喝,瞅準工夫就煉功,你給她銬上沒法兒煉了吧?她給你背甚麼經文。嗨,我都折騰累得跟孫子似的了,隨他媽便吧。」
鄒所長(陰險地):「大郭子,還得盯著她,看她絕食能挺到甚麼時候。有情況隨時告訴我。」
(二十三)
林心慧坐在黑暗的蹲倉裏,雙腳盤在一起,雙目微閉,面帶祥和,雙手戴著手銬,自然垂放在兩腿中間。
[畫面切換] 從日到夜,從夜到日,時間在流轉,林心慧依然祥和地盤坐在那裏。
(二十四)
看守所所長辦公室,鄒所長正翻著一本《大眾電影》,不停地往嘴裏填著花生米。
大郭子走進來對鄒所長報告說:「所長,這都七天了,那個305還是滴水不進、一言不發,再這樣下去,我們這兒可要出人命了。」
「怕甚麼,你不會給她灌食嗎?!」鄒所長眼睛依然不離雜誌。
大郭子(申訴冤枉似的):「呵,還灌食呢,甭提了!不是沒灌過,廢了牛大的勁
兒灌進去,完後她都有招兒給你吐出來,我認栽,幹不了了。」
鄒所長忽然覺出不妙,放下雜誌看著大郭子:「這麼說,對她沒轍了?」
大郭子(躲避著所長的目光): 「沒轍。你留著她這塊硬石頭,最後還是個輸局,」(忽然想出個主意):「乾脆把她扔出去得了。」
鄒所長(詭詰地):「你大郭子都沒了轍,我也得認這個頭不是?把她進來時候扣下的東西都留下,哄她走人!」鄒所長繼續舉起雜誌,往嘴裏填了一把花生米嚼著。
「她是北京的,不像外地來的帶那麼多的盤纏,總共也就帶了五十來塊錢,加上手錶也就值個二百來塊吧,都留下了。得,我提人去了啊。」大郭子晃著肥胖的身子走了。
(二十五)
林心慧戴著手銬,拖著虛弱的身子緩步走出牢門,她仰起頭,閉上雙眼,任憑柔和的陽光照在自己略顯蒼白的臉上。
大郭子給她打開手銬,「得,姑奶奶,走吧您那。我可告訴你,出去嘴頭子老實點兒,留神再給你抓回來!趕快走!」
林心慧盯著大郭子眼睛,一字一句地正告他:「你記住,善惡有報,你們欠下的每一筆孽賬,都將償還!」說完,她高昂著頭,緩步走出了看守所的大門。
(二十六)
燕園大學校運動場,彩旗迎風飄揚,身著各色運動裝的男女大學生們生龍活虎,躍躍欲試,比賽場上一片繁忙景象。
林心慧身穿一身潔白運動服,映襯著她紅潤的面頰顯得更加英姿瀟洒,她跑到了女子跳遠的集合場地。負責點名的體育組楊老師整理著隊伍,看到林心慧,他帶著懷疑、不解的目光問:「你能行?」
林心慧微笑著點了點頭。
跳遠場地,林心慧量好了步伐,站到起跑線上,她平靜無爭、認真自信,深深吸了口氣,開始助跑,速度加快,準確踏板,只見她身輕如燕,騰空而起,在空中動作舒展漂亮,之後雙腳落下……
負責裁判的楊老師驚訝地半張著嘴,隨著林心慧的落地,忽然醒過夢來似的高聲叫道:「好!漂亮!」他跑到林心慧跟前,拍著她的肩膀,「小林,我算是服了!七天的班房裏沒吃沒喝,你竟能跳出這麼好的成績,修煉法輪功的人真是神了!」
高音大喇叭裏傳來報告比賽成績的聲音:「現在報告女子跳遠成績。第一名,林心慧,成績……」
林心慧的周圍已經圍上了七、八個她的學生們,他們七嘴八舌、興高采烈地正在和林老師說著、笑著……
(二十七)
[字幕] 2000年6月23日
林心融的辦公室裏,林心融正在專心致志地做著財務報表,鄰桌的老徐正從暖壺裏往杯子裏倒水,桌上的電話鈴突然響起來,林心融拿起電話:「喂?」
「請問林心融在嗎?」電話裏是張大媽的聲音。
「我就是,您是哪位?」
[畫外音] 「我是你姐姐林心慧煉功點兒的,我姓張。我給你打電話是告訴你,林心慧幾天前和幾個人去天祥公園公開煉功,被公安分局的人給抓了,聽說她被刑警隊的人給打傷了,傷得很重,現在被送到白和醫院了……」
林心融驚異的面孔,直愣愣的眼睛,腦子裏一片空白,電話裏又說了些甚麼她甚麼也沒有聽見。
(二十八)
林心慧被從手術室裏推出來,護士把她推進了特護病房,病房的門口掛著一個牌子,上面赫然寫著:「病情危重,謝絕探視」。
剛剛完成手術的徐主任,筋疲力竭地回到主任辦公室,助理醫師和護士小劉也隨後跟了進來,剛剛坐下,公安分局的三個警察走了進來,「這是我們政保處孫處長」,一個警察指著另一個對徐主任介紹說。
「噢,孫處長。」徐主任站起身示意了一下又坐在椅子上。
「手術怎麼樣?」孫處長問道。
徐主任長嘆一口氣:「手術是完成了,但她的情況依然危險,我目前不敢保證不出意外,她傷得太重了。」
孫處長目光狡詐地看著徐主任:「不管出現甚麼情況,我們都是自家人嘛,對外說話要把握分寸,該說的說,不該說的就不說,要給自己留有充份的餘地,您是大夫,這一點,我想您一定心裏有數,是吧?」
徐主任靜靜地坐著沒說話。
孫處長:「這個林心慧目前還沒有解除拘留,她還在我們的監管之下,因此病房門口要留人看守,任何人探視必須經過我們的許可;另外,她的診斷病歷,必須在我們的監視之下,由醫院保衛科封存。」
徐主任還是靜靜地坐著不說話。
孫處長看對方沒有任何反應,臉上堆起些乾笑:「你們也辛苦了,休息吧。」說完,自覺沒趣地走了。另兩個警察尾隨而去。
護士小劉見警察們走遠,不滿又不解地:「他們對一個癱瘓的危重病人犯得上這麼戒備嗎?」
「你不知道,林心慧是個法輪功學員,被他們抓進去的,人傷成這個樣兒,還不知他們是怎麼整的呢,這背後有事兒!」助理醫師悄聲道。
「小劉,注意觀察林心慧的情況,醫護筆錄要盡可能細緻。唉,不通知家屬,真是說不過去啊。」徐主任囑咐著護士,走進內室更換手術服。
(二十九)
還是那輛由哈爾濱開往北京的火車上,林媽媽手捧女兒林心慧的照片,凝望著車窗外灰色的天空,漸漸地陷入了回憶……
「你是幼稚!不知深淺!拿著雞蛋往石頭上撞!」林媽媽家客廳裏,林先生一臉怒氣站在客廳中央,紅著臉對林心慧大聲訓斥著。
林心慧平靜地坐在沙發裏,眼裏充滿慈善地看著爸爸,林心融攙著媽媽站在一邊,林媽媽看上去十分焦慮不安。
林心慧站起身走向林先生,「爸爸,我是搞法律的,我知道上訪符合憲法和法律,上訪是公民的基本權利之一,我沒有做錯任何事,我只是想通過我的行動,告訴政府,同時告訴善良的人民,鎮壓法輪功是錯誤的。」
林先生依舊激動地大聲吼道:「這是政治,我的大小姐!政治是用人血灌溉的荊棘!在強硬的政策面前老百姓的權利一文不值!別說你是個普通小民,國家主席怎麼樣?不也照樣打你個『叛徒、工賊』嗎?不也照樣冤死?文革的罪我們家已經受夠了,……」
[畫面隨著畫外音切換] 「你爺爺被造反派打死,你奶奶被逼瘋,你大姑被折磨成殘廢,你爸爸我在勞改農場裏險些病死……」
(林先生面部悲愴的特寫)「如今,你又要往槍口上撞,不行!我告訴你,就是不行!」
一切聲音突然中斷了,靜,時間好像停止。
林心慧看著情緒激動的爸爸,口氣平和地對爸爸說:「爸爸,法輪功上訪就是為了不讓這樣的災難再發生啊,我們不能再看著好人受害,壞人瘋狂。如果面對邪惡,沒人敢出來說句公道話,國家會成甚麼樣?人民又如何能安居樂業呢?」
林心慧走到爸爸跟前,用手去攙扶還在微微顫抖的爸爸:「爸爸,法輪大法給了我健康的生命,更讓我懂得了如何做人,我不能在大法遭受迫害、善良人遭受苦難的時候只想到自己,在這樣的時候,我的心告訴我應當作出甚麼樣的選擇。」
林先生甩開了女兒的手,面對著女兒繼續說:「呵!你高尚,你偉大,你是不知道共產黨政權的殘酷!你現在被停職、降薪,再這樣下去,你還會被開除公職,甚至會被逮捕判刑!你那三尺之軀面對整部國家機器,就像一滴水掉在燒紅的烙鐵上,你就這樣報答養育你的父母雙親?!」
林心慧望著年過花甲的父母,她的心在顫抖,她一時無語,眼淚順著面頰流下來。
林媽媽抹著眼淚,走過來對林心慧說:「孩子,媽媽知道你護法的心,也希望你能體諒爸爸愛子的心,爸爸文革中吃苦太多了。我只有一句話,你做事一定要冷靜、謹慎,在這大是大非面前要對得起自己的良心。」
林心慧含著眼淚,面對著養育自己的父母雙親,充滿真摯地說:「爸爸,媽媽,我熱愛養育我的父母,我也熱愛自己的家。可是如果天下所有的父母和家庭因為一種罪惡而蒙受妻離子散、家破人亡的苦難,我們怎麼能無動於衷呢?」
林心慧擦乾臉上的淚,堅定而祥和:「爸爸,媽媽,法輪大法蒙茵整個社會,救度善良世人;大法給了我新的生命,我要對大法負責啊。雖然我很渺小,但我是大法中的生命……」
「嗚──」,長鳴的汽笛把林媽媽從回憶中驚醒,她不再流淚,臉上充滿安寧。
(三十)
北京火車站。林心融焦急地等在站台上,一會兒看看手錶,一會兒望望列車將要開來的方向,在站台上來回踱著步。
一聲汽笛長鳴,從哈爾濱開來的列車緩緩駛入北京站。
林媽媽和林先生相互攙扶著下了列車,林心融迎過來對父母說:「媽,爸,姐姐已經動了手術,住在白河醫院裏,我們直接去醫院吧。」三人邊說邊出了站。
一輛紫紅色的桑塔納開過來停在正在招手叫車的林心融跟前,林心融照顧父母坐在後座上,自己坐到前排副坐上對司機說:「去白河醫院。」 車子啟動,離開了人群熙攘的北京站。
(三十一)
手術後的林心慧躺在特護病房裏,點滴吊架上掛著輸液瓶,呼吸導管接著呼吸機,吸氧管插入鼻孔用膠布固定在嘴邊,心臟監視器顯示著有規律的心跳節律。帶著大口罩的護士小劉正在查看著輸液瓶和呼吸機。
林心慧閉著眼,左眼上蓋著一塊潔白的紗布,喉部插著的呼吸導管用層層紗布纏繞在脖子上,她半張著嘴,看不出她的神志是否清醒,一張白單子蓋住大部份身子,露出的腿上和腳腕處,紫塊兒和傷痕依稀可見。
護士小劉推門走出了病房,只見一個身著便服的男子守在門口,手裏拿著對講機,面呈栗色,目光詭詰。他身上那股特有的味道,讓人一看便知是便衣警察。
林心融陪著媽媽、爸爸來到走廊,迎面看到護士,林心融上前打聽:「請問林心慧住在哪間病房?」
小劉停下腳步,睜著大眼上下打量著三個人。林媽媽趕緊解釋:「我們是林心慧的親屬,剛從哈爾濱趕回來,她現在情況怎麼樣?能不能讓我們看一看?」
只見小劉的頭往便衣那兒一晃,「瞧那兒,探視的決定權不在我們這兒。」
「怎麼?人傷成這樣,她是病人,醫院怎麼會不能決定讓家屬探視?」林心融有點激動。
「你們來吧,跟主任說說。」小劉引著林心融一家來到醫生辦公室,「徐主任,林心慧的家屬來了,要探視,您看怎麼辦吧。」
「大夫……」林媽媽上前欲對徐主任說甚麼,徐主任舉起手制止了她,然後透過窗子看看辦公室門外,走過去關上門,轉過身來對林媽媽說:「您女兒的情況非常不好,也非常特殊,您看到了,特護病房門口的看守,那是公安分局特別安置在那兒的,他們有話,現在任何人探視,必須得到分局的批准。」
林心融憤怒不已:「真是豈有此理!我姐姐不是罪犯,她只是到公園裏煉功,就把她給折磨成這樣,我們家屬沒從公安分局那裏得到任何關於姐姐的消息,是單位和朋友通知我們才知道姐姐已經住進醫院,他們有甚麼道理不讓家屬看病人?!」
徐主任嘆道:「真對不起,你們的心情我做醫生的非常理解,可我們也是無能為力啊。」
「心融,你冷靜點兒。」 林先生問徐主任,「大夫,您能不能告訴我們,她是甚麼時候、怎麼被送來的?當時情況甚麼樣?」
徐主任:「她是前天下午被白河公安分局的人送來的,我接手的時候她雖然神志清醒,但人已處於癱瘓狀態。」
「我們被通知她病危,她到底傷成甚麼程度?有生命危險嗎?」林先生繼續問。
徐主任解釋道:「林心慧的第四、五、六三節頸椎骨粉碎性骨折,是極其嚴重的頸椎損傷,它同時引起對呼吸和神經系統的損傷,隨時會有生命危險。這就是我們發病危通知書的原因。她需要做手術,氣管兒切開後將有一段時間不能說話,我們當時就已經跟分局的人講清楚,讓他們馬上請家屬來。」
林先生充滿期望的雙眼看著徐主任,問道:「徐主任,您是醫生,您能不能告訴我們,從醫學角度看,造成三節頸椎粉碎性骨折的原因會是甚麼?心慧她現在情況怎麼樣?」
護士小劉警覺的目光看著徐主任。徐主任也看了看小劉。
片刻沉思之後,徐主任慢慢言道:「你們了解體操運動員桑蘭在美國摔傷的情況嗎?她是做跳馬時騰空後失手,從高空摔下來造成一節頸骨骨折、半身癱瘓的。像林心慧這樣四、五、六三節頸骨粉碎性骨折的病人,在我的經歷中還是第一例,如果不是人為的、來自外力的強烈行為,很難想像會造成這樣嚴重的損傷。」
徐主任深深地嘆口氣,接著說:「你們家屬要有思想準備,目前她雖然經過了手術,但並沒有完全脫離危險,即使能保住生命,她也會是終生高位截癱,恐怕──頭以下的任何部位都將失去活動功能。」
林媽媽痛哭失聲,「慧兒,你冤啊!」她滿臉淚水,不能自已;林心融抽泣著,攙扶著母親坐在椅子上。
「一幫野獸!我要告他們!」林心融強壓著自己的憤怒。
林先生眼裏噙著淚水,對徐主任說:「我們能不能看看她的診斷病歷?」
徐主任(沉痛而遺憾地):「林先生,我非常對不起,分局的人已經下令,看病歷也要通過分局的批准,他們已經把林心慧的診斷病歷交給保衛處封存了。」
林先生無助地抬起頭,帶著無限的悲憤呼喊:「天啊!他們還有沒有人性,還講不講天理啊!」
[畫面] 一聲霹靂,雷聲隆隆,陰沉沉的天空灑下淚雨,花兒低垂著帶淚的頭,樹木掛滿晶瑩的淚珠,大地浸潤在上蒼的淚水之中。
(三十二)
﹝字幕﹞兩天以後
林媽媽夫婦和林心融又來到醫院,徐主任再次接待他們。
徐主任:「我們和白河公安分局多次打招呼,林心慧的情況需要24小時貼身護理,單靠我們醫院的人力已無法解決,這確實是個實際情況,分局的人已經同意親屬探視和參與護理。」
林心融(焦慮地):「我姐現在的情況怎麼樣了?」
徐主任:「危重情況有所緩解。她真是不可思議,精神很頑強,好像生命力也很頑強,說實話,起初我始終是不報希望的,這麼嚴重的損傷,極其危險,倖存已是奇蹟。當然,她仍然處於危重階段,仍需要特別護理,氣管切開術使她現在還不能說話。」
林媽媽急切地問:「我們現在能去病房看她嗎?」
徐主任:「走吧,去看看她。最好不要引起她的情緒激動。」徐主任在前帶路向病房走去。
林心慧躺在雪白的病床上,雙目微閉。林心融、林媽媽和林先生來到她的床邊。看到女兒危重的樣子,林媽媽抑制著自己的悲傷,用手緊緊捂住自己的嘴。
林先生輕輕地為林心慧蓋好單子。
林心融見姐姐毫無反應,便輕聲問徐主任:「她的神志清醒嗎?」徐主任點了點頭。林心融貼近姐姐的耳朵,輕聲叫道:「姐姐,姐姐,我們來看你了。」
林心慧無力地微微睜開眼,看見媽媽、爸爸和妹妹,淚水順著眼角慢慢地流下,滴到枕邊。
林心融輕聲地在姐姐耳邊問道:「姐姐,你是被人打成這樣的嗎?姐姐,你如果是被人打成這樣的,你就閉一閉眼睛告訴我。」
只見林心慧慢慢閉了兩次眼睛,她用自己唯一能用的方式揭露著邪惡,聲討著罪惡的迫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