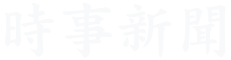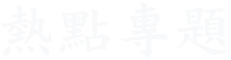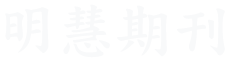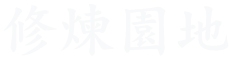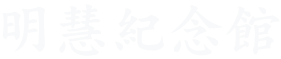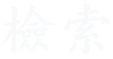我在北京馬坊派出所遭受的折磨
我在家略加準備,帶上「法輪大法好」條幅在月色下向北京方向起程了,沿路警察、便衣遍布車站、路口。我由徒步、坐汽車、倒火車幾經輾轉終於到達北京。北京的各旅社沒有身份證一律不讓住宿,白天我們在郊區的山上背經文,到晚上天氣很冷,找一些拆毀的民房過宿或出高價宿於有善心的民眾家。第二天天不亮就得走,怕連累無辜的百姓受當局迫害。
在天安門廣場,我接過被惡警打倒在地的法輪功學員手中的條幅,展開後就向北跑,發自內心地喊出了「法輪大法好!」當時剛升過國旗,廣場上人山人海,大法弟子喊成一片,此起彼伏。惡警手持膠棒、皮帶等凶器不分男女老少,猛打猛踢。有的大法弟子當場被打的血流如注,嘴和眼被打得腫脹、變形。但沒有一個大法弟子自衛還擊的,也沒有出言粗魯的,只看到聽到大法弟子的正義呼喚和極限的承受。
我們大批大法弟子被抓到天安門派出所的一個大院內,這裏的惡警更是壞,用膠棒、木棍專向大法弟子的臉上頭部猛打。不長時間它們用大客車拉我們轉了不少監獄,把我們囚在院內的大鐵籠子裏又是照相又是叫按手印,逐個編號,一個個過關,稍有不從就上來幾個人拳打腳踢。它們真的是往死裏打大法弟子。最後它們把我們大法弟子2-3個分成一組,讓北京各地派出所拉走。
我和一位同修被拉到一個叫馬坊的派出所。惡警把我銬在屋內桌子腿上,然後開始問我姓名和住址,我不說,一個胖惡警、一個黑大漢就對我殘酷折磨。它們倆輪番的在我臉上猛打,拳腳相加,也不知打了多長時間,只覺得臉發木,全身發熱。胖惡警的手都打的疼了,它無人性的用手銬往我臉上摔,用肘猛擊我的背部,用我帶的1.5寸小刀刺我的臀部。它們倆對我折磨了半天,甚麼也沒有問出來。它們就使出最後的毒招,讓我和另外一名同修脫去衣服,銬在刮著刺骨的寒風、下著小雪院內的小竹竿上凍我們。凍了我們兩次,每次足有兩個小時。它們當官的怕出人命不好處理,才讓惡警鬆了銬。這樣也沒就此罷手,把我帶到鍋爐房,打開爐蓋,讓我靠近爐口烤我。噴出的火舌烤的我實在難以忍受,就向後退,惡警在後邊用拳打我,不讓我退。
烤了前面烤後面,還讓我看著它的眼睛不能動,還得面帶微笑。烤的我噁心的嘔吐,還得咽到肚子裏,否則就一陣毒打。在看鍋爐的老頭勸說下才讓我退了下來,並往我的臉上狠搧幾下說:「在外邊凍冷了,讓你在這兒暖和暖和,你小子就不給我面子,一句話也不說,打你活該。你再不說住址、姓名,到晚上把你埋到後河沙灘裏,報你一個無名屍體就完了。再不就送你去大西北監獄,從此你就從這個世上消失了。」它們在打我的同時,使我最難受的是它們罵我們師尊、罵大法,並說:「××黨從不信神不信鬼,就信不打你們江××就讓我們下崗。你們要是死了,到閻羅老頭那裏不要告我們的狀,你們要告就告江××,是江××叫我們幹的,我們都有文件和命令。」
它們讓我穿上衣服,此時已是下午的5點多了,看樣子它們準備送我到大監獄。這時胖惡警給一個當所長的說:「打通啦,他的哥哥承認他這個弟弟。」原來它們搜走了我帽子夾縫中的電話號碼,並對我說讓你哥來認一下,把你帶走。我怕連累親人遭受無辜的迫害,無奈地說出了我的地址。它們如獲至寶般的給我們地區駐京辦打去電話。當地駐京辦把我帶到辦事處小屋裏,裏邊早有縣公安局的惡警守候在那裏。進門把我和另一名同修背靠背銬在一起,問我是哪個村的,叫甚麼名字?我沒理它們。有一惡警用穿著皮鞋的腳向我的胸部猛踹了幾腳,向臉上踢了兩腳。當晚後半夜用車將我們三名大法弟子銬在車內拉回縣公安局拘留所。在拘留所也受盡百般折磨。每天交10元生活費,吃的是小饅頭、爛菜湯。上廁所受限制,能睡5人的小屋卻讓十幾個人睡。人多的時候,大法弟子把被子和炕讓給進來的常人睡,自己睡地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