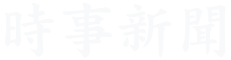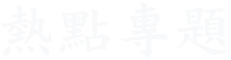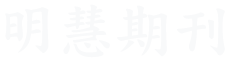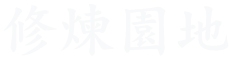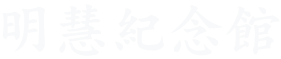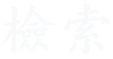退休老軍人4.25後遭到的「全方位」監控
【明慧網2003年4月17日】我是年近古稀的退休軍人,法輪大法修煉者,我來講講我因修煉而受到的全方位監視、跟蹤的「待遇」。
99年4.25後局勢日趨緊張,在院內多年的煉功點被勒令停了下來。我們無奈被迫到大街上馬路邊煉功,一直遭到公安、居委會、單位的盯梢、數人頭,公安到家裏查看、摸底。單位領導到家裏「做工作」,找來一些老同志、老同事談話,施加壓力,說根據上級要求:「××黨員、軍人一律不能煉功」。
7.20後,「黑雲壓城城欲摧」。區民政科、居委會等多個單位聯合起來多次到我家騷擾,勒令交書、寫「保證」放棄修煉。派出所開著車到家裏窺視,不容分說將我帶到派出所進行審訊筆錄,像楊白勞一樣在筆錄上多處按手印,實屬我一生中第一次。其實區民政科、居委會、派出所的這些行為連他們自己的規定都不符合,軍人應由部隊管理,地方到部隊插手,豈不亂套?
部隊則大會、小會直至黨委擴大會進行談話,施加壓力;一到「敏感日」則派數人到家裏談話。還限制人身自由,多次深更半夜打電話,查對是否在家。退休了還規定外出請假,由開始的「到北京請假,其它地方不管」,到後來「外出一律請假」、「只能在市區活動,出市就請假」。門衛為了能認準人,還親自到家裏認人。
2000年國慶節後,在預先給單位幹部打招呼去北京的情況下(我愛人家在北京,以前我也經常在北京),一出門就被跟蹤。而且人剛到北京,他們就從家人那裏得到電話號碼,電話就跟到了北京。後學院派車,我的上一級幹部一把手親自帶人就跟到了北京。無奈,我在北京只呆了40個小時就回來了。上車由他們親自看著上車,回來由他們派車去接,只因沒接上,還虛緊張一番。
(c)2024 明慧網版權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