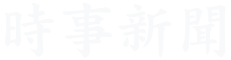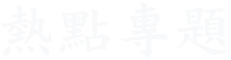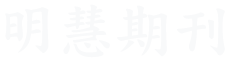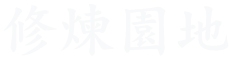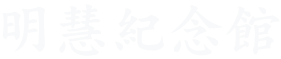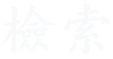修煉中要放棄執著
在《轉法輪》的「煉功招魔」一節裏,師父教導我們:「因為人有情在,生氣是情,高興是情,愛是情,恨也是情,喜歡做事是個情,不喜歡做事還是個情,看誰好誰不好,愛幹甚麼不愛幹甚麼,一切都是情,常人就是為情活著。那麼作為一個煉功人,一個超常的人,就不能用這個理來衡量了,要突破這個東西。所以有很多從情中派生出的執著心,我們就得把它看淡,最後完全放的下。慾和色這些東西都是屬於人的執著心,這些東西都應該去。」
我的理解是,我們的修煉是放棄自我利益,溶入一種無所求而自得的狀態中,我們不能執著於自己想做甚麼,即使自己想做的是好事。因為每個執著都要放棄,不僅是為了個人修煉,自己的執著也會干擾正法。
為了闡述這一點,我想說說我參與神韻藝術團演出的一些歷程。那還是在第一年的演出,叫做「華人新年晚會」的時候。第一年的歐洲合唱團同修合唱的《為你而來》在紐約獲得輝煌的成功後,就要來到華盛頓DC演出了,需要我們華盛頓DC本地的一些人充實合唱團。我從來沒說我是個好歌唱者,一開始也感覺讓其他任何人唱都行,但是大家告訴我他們的確很需要人,不管水平如何。並且這首歌是為西方人去天安門那件事而創作的,那麼有我這個當事人參與合唱也挺好的。所以我決定全心投入其中。
那一年,我的弟弟和我都是同樣的情況。我們和住在我們家裏的其他同修們天天練,天天學,天天討論。我感覺是那麼的神聖,能成為其中的一粒子是那麼的殊榮。但是,哎,世事難料。在演出開始的前一週,我弟弟和我被告知,我們唱的不夠好。實際上,我被告知,我在音調上基本是個聾子。我和弟弟是僅有的兩個被涮下的,而且我猜測我弟弟的被涮,是為了避免我們倆只有一個在合唱團。那是早在二零零四年的事,那時我弟弟和我曾經天天早上去中共大使館前發正念和煉功。我記的在被合唱團涮掉的前幾天的一次打坐中,我感覺我將要被涮掉了,我接受不了,甚至連打坐時也接受不了,我哭了。
想到不能成為那個令人驚嘆的、美麗純潔的團體的一粒子,我就很傷心。我想在台上為救人而歌唱。但是即使這是個好的願望,也開始變成了執著心。
我從來沒有因為努力做救人的事而被拒絕過。這看起來是那麼的矛盾,但是我不得不想,如果師父想讓我唱,他一定會很容易的改善我的聲音,所以我不能執著。這是一個不斷的使自己變的謙遜的過程,我記的我和弟弟在最後的幾次感到羞辱後,不停的笑啊笑啊笑,從此我們明白了那些是多麼的荒謬,明白了我們真的是被考驗了一把。
那是頭一回我想盡力做好一件好事,但是結果卻被不允許去做。二零零五年,我出國了,所以沒能參加那一年的晚會。二零零六年我參加了,那一年我成為了晚會主持人。那是很難的一個任務,儘管我有演出的經驗,經常主持新聞發布會、集會和其它活動,但是主持晚會就是另外一回事兒了。
這個任務困難的地方在於它本質上是無私的,你的任務僅僅是介紹真正的表演者。沒有人看演出是來看主持人的,是吧?所以要做好,必須對此有很深的認識,要把主持溶入節目的情節中。你所有要考慮的就是突出那些偉大的藝術家們,但是我很難找到時機和演員相處和了解,和我的搭檔主持人一起設計主持詞。直到最後,在第一場演出就要在波士頓開場的前一夜,我們有一次穿服裝的彩排,可能今天這裏就有一些人參加了那次彩排。我不得不說,我的主持差的可怕,所以我和搭檔幾乎一夜沒睡,在其他同修的幫助下,我們徹底修改了我們的主持稿並在實際的演出中表現很好。
一個城市接一個城市,一場接一場,我們在不斷的提高。我感覺我們在很好的幫助觀眾被演出救度。但是在紐約演出時,協調的同修們決定讓別人來代替我主持。他們甚至讓那個人從國外大老遠的趕過來,我感到莫名其妙,因為他們從來沒有表達過對我的表現的不滿,並且那個主持人也是要用和我一樣的主持詞,甚至他們從來沒有給我一個解釋。他們僅僅是問我是否可以幫那個主持人做到最好。
不用說,我的自尊被傷害了,並且又一次的,我被丟在一邊兒納悶:為甚麼這麼一件輝煌壯麗的事情,我卻不被允許去做?甚至這一次我是有能力去做的,不像上次唱歌那樣。但是表面的不同並不重要,從根上,我仍然不得不放棄我想去配合的事情。
在紐約的演出中,在這次最大的一場巡迴演出中,並且是在國家最著名的劇院之一的演出中,我站到了後台,做主持人的助手和跑腿兒,偶爾給些建議,力所能及的幫幫忙,試著以苦為樂。
二零零六年巡迴演出結束後,我決定提高主持水平,這樣才會和天天訓練的舞蹈、歌唱、和樂器演員們相配,我想成為下一年演出中最好的主持人。我上了表演課、聲音訓練課、芭蕾課來提高我自己;我鍛煉和節食,減掉了二十磅;並且對我知道的下一年的節目開始考慮主持詞了。但是在十一月的一天,一個協調人說他們仍然在考慮主持人選,難道還有主持人不是我的可能?我很震驚。沒有人曾經說過任何這方面的事,並且我準備了一整年。我知道這是一個考驗,我得順其自然,但是事情變難了。
那一年,巡迴演出是從十二月紐約的聖誕奇觀開始的,並且二零零七年的巡迴演出將花上幾個月的時間,所以要成為主持人,我就要辭職。我並不介意辭職,但這得是在需要的時候,我才會去辭職。那時離巡迴演出開始只有一個月了,我開始詢問是否需要我主持,但是突然間,沒有人回應我的電話和電子郵件了,我得不到任何回答。最後,在十二月的第一天,我需要決定是否辭職了,我最終明白了我僅僅是需要盡力把自己投入演出中,即使我還不知道我是否是三個星期後開始的歷時三個月的演出的主持人。於是我辭職了,然後幾天後,我就接到了協調人的電話,說主持人不是我,並且他們不需要我。
我很失落。我脫離了一切其它的項目和我的工作,我真的不知道該怎麼做。我決定去紐約幫助賣演出票。上一年,我站在劇場後台吞食我的自豪;這一年,我站在劇場外的寒冷中做著同樣的事情。
我的媽媽住在英國,每年聖誕節都來看我,所以那一年,我告訴她得去紐約,她可能在舞台上看到我。當她發現我沒有參加演出時,她有一點失望,但是她已經花錢定了機票和旅館,我也真的很想讓她看看演出,因為演出可以救人。但是我知道我仍然對那些協調人有著無法消化的敵意,所以在媽媽到來之前,我去看了首場演出。我想通過看演出來消除我的壞思想,因為我不想讓我的沮喪來傷害我的媽媽和其他的觀眾。我坐在觀眾席上,為整場演出發著正念。演出結束了,觀眾都離開了,我還是坐在那裏,還在試圖去掉我的執著。我知道我需要向前走,放下執著,所以我等在舞台的門外,直到和我在主持上合作過的協調人出來。我想他們很吃驚的看到我站在那裏,因為他們幾乎是最後離開劇院的。我只是告訴他們,我認為演出太棒了,他們做的很出色,謝謝他們努力的工作。
接下來的幾天裏,我繼續在紐約的大街上推廣演出,並且我發現我在幫助更多的眾生得救,這種感覺使我很受安慰。總之,如果我主持節目,我就不可能站在大街上推廣演出了。當我和其他同修交流這個想法時,她非常和善的告訴我,能放棄當主持人的想法,僅僅去想著救度眾生,這非常好。但是我還是需要再提高。她告訴我她很羨慕我有這個放下自我的機會,我應該珍惜這個機會。那一年我得到了不少啟示。
二零零八年的巡迴演出,我寫了很多推廣演出的資料,比如海報、傳單和網站。我做英文大紀元的編輯很長時間了,在常人中也是做媒體工作的,常常寫一些宣傳資料,所以我覺的很喜歡並且很適合做這些事情。這又是一個提高的好過程,充滿著挑戰和奉獻。去年在這個過程結束後,我決定在今年提高,試著早早的把很多想法寫在紙上。我也試著和其他主動要求做寫作工作的同修交流我的更多的想法。
但是,不久前,有人說因為他們不喜歡去年宣傳稿的質量,他們想讓另外的人來寫稿子。我想,好吧,今年這個組的規模大了很好啊,我們能有更多的人做真是太完美了。顯然我沒有理解他們的言外之意,因為不久協調人就停止回覆我的電子郵件,並且不喜歡和我討論有關寫作的想法了。
現在我將去宣傳的另一種形式──網站工作了,但是不停的改變方向,改變我在項目中的角色是困難的。我幾乎沒有參與過協調人的決策過程。這就像在拼圖遊戲中,只給我了幾小塊兒拼圖塊兒,而我需要試著找出這些圖塊兒應該怎樣和其它圖塊兒拼合。但是卻沒有人知道這些圖塊兒最終要拼出的模樣。
最近在我們做講真相的工作時,我的一個類似的經歷提醒了我要徹底放棄自我。我住在華盛頓特區,紐約相對來說很近,所以當紐約法拉盛的暴徒們騷擾和攻擊法輪功學員的時候,我真的感到我應該週末去紐約。但是幾個星期過去了,我忙於在華盛頓的大法工作而一直沒有去成。幾個星期後,我被請去幫忙整理製作要在紐約散發的法拉盛版的《今日法輪功》的報紙。工作了兩整天後,我告訴另一個同修,我現在感覺好多了,好像我為幫助法拉盛做了我該做的。幾年前我沒能當上主持人時,也是和這個同修交流的。她向我點出,這種想法可能也反映出我在一定成度上的自私,不是單純想著救度眾生,而是看重我自己對救人的貢獻,我仍然還有的修。
想當合唱團員,想當主持人,想當作家,在這個過程中我經歷了很多的執著。但是從根上是對自己的執著,是去做我自己想做的事。儘管我想做的是好事,但我的修煉比做好事還重要。
在《轉法輪》的「修口」一節中,師父說:「咱就說一般的,我要幹甚麼幹甚麼,現在這件事該怎麼做怎麼做,可能無意中就傷了誰。」
難道不是師父在帶著我們修麼?如果我們按著自己想的修,也許我們就會不經意間傷害到甚麼,就成了舊勢力那樣只想得到他們想要的而不是正法。
師父在《北美巡迴講法》中說:「那麼舊的勢力到底和我是甚麼關係?我就講講這個問題。其實呢,這些舊的勢力啊,嚴格的說,它們不是為了毀掉正法這件事情,它們也不敢毀。它們的目地,雖然不純,它們也想要使正法這件事情能夠成功,只不過是它們要這一切按照它們要求的做,按照它們的要求正法,那是絕對不允許的。」
師父還說:「在幫我的同時它們都隱藏了保護它們自己的私心,都想要改變別人而不想改變自己,誰都不想動自己,甚至於最大限度的保全自己執著不放的東西。整個過程中有很多事它們幹的都非常不好,有些它們是有意幹的,而有些它們自己都意識不到是很壞的事情。」
我的理解是,執著自己是宇宙出問題的根本原因,也是要正法的原因。我也想到當我們不放下我們自己的執著時,我們不僅在阻礙著自己的提高,不僅在阻礙著救度這特殊時期裏依賴我們的眾生,我們實際還在干擾著正法。如果執著的時間太長了,我們甚至會在一直想要做好事的念頭中,給眾生帶來危害。
謝謝大家,謝謝師父!我會在您為我安排的修煉路上走的更好。
(二零零八年華盛頓DC法會發言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