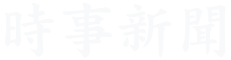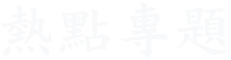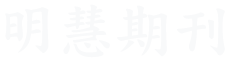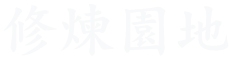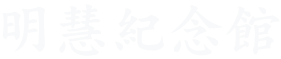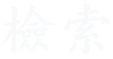請律師營救同修的修煉感悟
然而因為此事,我和丈夫同修就開始關注明慧網上關於運用法律反迫害方面的內容,我們漸漸認識到運用法律反迫害是一件非常有意義的事情,如果做好了,不但能真正的營救同修,更重要的是,能通過這種方式震懾邪惡,制止迫害,救度公檢法司人員。從法律上反迫害,更能讓民眾看清邪黨知法犯法的強盜嘴臉,人間的法律不是給邪惡逞兇的工具,我們大法弟子應該歸正它,行使法律的真正使命──懲惡揚善。
或許一切都是有安排的。二零一六年,本地一名同修被綁架,同修A又找到我和丈夫,提出要請律師營救同修,我和丈夫就順理成章的擔起了請律師營救同修的任務。從那之後三年的時間,我們共負責了六場請律師營救同修的官司,接觸了數位律師,場場官司都不一樣,有些狀況甚至錯綜複雜。過程中有喜有悲,有慘痛的教訓,也有經驗的積累,有矛盾中不知所措的迷惘,也有明晰法理後的正念正行。方方面面的感悟都很深,但是因為篇幅有限,我想僅從與律師的配合這一方面來交流一下經驗教訓和心得,與同修們交流。
一、只做完全、徹底的無罪辯護
大家都知道,常人打官司請律師,只是為當事人本人減輕刑事責任。而我們大法弟子請律師,雖然也是為了營救同修,但是還有更深遠的維護大法、救度眾生的意義,那麼必須是基於修煉大法無罪這個最基本的前提。所以,我們都知道請的律師必須是做無罪辯護的律師。在這個大的前提下,對請來的律師自然都是很放心和信賴的。能為我們做無罪辯護的律師基本上都能認清邪黨的本質,對大法有正面了解,並且有正義感、社會責任心。所以,二零一六年,接觸第一位律師時,我們都很信賴他,因為他說他自己讀了一些師父的經文,以至於後來我們有點像同修一樣相處了,而忽視了一個事實,他還是個常人,思維中都是常人的觀念。
當這位律師在為一名老年教師同修做辯護的時候,在做完無罪辯護之後,又做了有關量刑辯護的陳述,大致意思是:「在我堅持認為我的當事人無罪的前提下,鑑於我的當事人年齡較大,為教育事業做了一輩子的貢獻,希望法官在量刑方面予以考慮。」
開庭當天,去了一些同修,現場的同修當時就對這位律師的辯護很不滿意。我們當即找到律師,律師解釋說,他在看守所被老年同修想回家的人情帶動,按照律師慣有的思維,覺得做一下量刑辯護對被非法關押同修有益處。他一再強調他做的是無罪辯護,並把辯護詞給了我們。我們雖然理解律師想幫助被迫害同修回家的心情,但是明顯感覺這個量刑辯護有悖於我們修煉大法無罪的初衷。
在後來的另一場官司中,我們吸取上次的教訓,對另外一位律師提前講明只做無罪辯護,不做量刑辯護。沒想到這位律師善意的提出了不同意見,認為無罪辯護和量刑辯護並不矛盾,並說如果不做量刑辯護的話,卷宗都沒必要仔細看,既然無罪那就對所有「證據」一概否認就行了,如果做不到無罪釋放,就只能任其重判。聽了這位律師的說法,我們意識到這不只是個別律師的誤區,很有必要對此問題進行系統的梳理,與律師深入溝通,形成共識,這樣才能把營救同修的事做到位,達到救人的效果。
我和丈夫查閱了關於這方面的法律知識,又從修煉的角度,在法理上深入的交流了這個問題,寫了一篇《關於律師是否做量刑辯護的交流》的文章,後來這篇文章發表在明慧網上。文章中明確指出:「辯護律師在法庭上,針對大法弟子被構陷的案件,只能做徹底的、純粹的無罪辯護,量刑辯護就是不同程度的妥協,而金剛不動的大法弟子面對邪惡的迫害不接受任何妥協,是從根本上否定的。」
那麼,如果我們要求律師只做無罪辯護,不做量刑辯護,是不是就像前面律師所認為的那樣,對邪惡構陷大法弟子的卑鄙手段和捏造的所謂「證據」不理不睬了呢?就任由邪惡對大法弟子肆意迫害呢?其實並不是這樣的,這恰恰說明律師並沒有真正領會同修請他打官司的目地和意義所在,這就需要我們進一步的向律師講明真相。
中共邪黨的邪惡之處,就在於它一方面幹著傷天害理的惡事,一方面又冠冕堂皇的掩蓋著。其實,參與迫害大法弟子的公檢法人員心裏都知道是在走過場,在庭審之前,六一零把刑期都定好了,他們很多人也為虎作倀,以固有的思維認為大法弟子可以任由他們迫害,可以在所謂辦案過程中,肆意捏造證據進行構陷。在這種情況下,如果辯護律師從法律專業的角度,把惡人所有不合法、不合規的地方全部都揭示出來,就等於是剝下了邪惡者的畫皮,讓所有參與的人員,看清邪惡者的本質,從人的層面上震懾邪惡因素,從而喚醒他們的正義感。
儘管參與迫害的公檢法人員被中共謊言所欺騙,為利益所驅使,成為中共迫害大法弟子的幫兇,但是他們也是受害者,等著我們大法弟子救度。如果在大法弟子和辯護律師的正念配合下,在事實和真相面前,他們能夠良心發現,擺脫邪惡的控制,做出有利於大法弟子的正義判決,那也是他們為自己選擇了美好的未來,這才是大法弟子請律師打官司的真正目地和意義所在。
那麼,從這個角度來講,我們必須讓律師清楚的知道,我們不做量刑辯護,但我們希望律師能夠當庭揭露公檢法人員的違法行為,為大法弟子做完全、徹底、有始有終的無罪辯護。
通過寫這篇文章,我們自己的思路也清晰了。在後來的律師配合中,我們都按照這個原則去跟律師溝通交流,引導他們按照我們的路子走,事實證明在後來的幾場官司中,律師發揮了極其重要的作用。
二、充份發揮律師的作用
通過一段時間的配合,我們漸漸明晰了律師在我們這個項目中應該擔任的角色和能夠起到的作用。利用律師這個特殊的身份為我們的營救工作充份發揮作用。
首先,我們可以通過律師與被關押的同修進行交流、加強正念。二零一八年,我身邊熟悉的一位同修被綁架,在非法庭審前五個月時間,律師總共會見了同修八次,每次我都提前準備好與同修的交流信,讓律師會見時念給她聽。因為我非常了解這位同修,清楚她的修煉狀態,所以我寫的交流信很有針對性,對她加強正念、向內找都有很大的幫助。並且這位律師的悟性很好,會背很多師父的經文,經常給同修背誦經文,鼓勵同修的正念。同修出來後,回憶說,那段時間,律師的會見對她幫助很大。
因為一般請的都是外地律師,所以不是每一位律師都有空暇時間經常來會見同修,這需要和律師溝通,根據需要的具體情況來安排。同時考慮律師的營利需求,如果需要增加律師額外的工作,我們通常除了路費還會補給一些相應的費用。
其次,律師在會見公安人員、檢察官、法官時,可以從法律的角度向他們講真相。這個環節很重要,但是不同律師做法不同,用心程度不同,起的作用也不同。二零一七年,一位老年同修被非法關押期間,老伴突發重病住院,同修的不幸遭遇牽動著參與營救同修的心。這時同修的卷宗已經到了檢察院,我們給律師增加了費用,希望他能以他的身份發揮更大的作用。律師很用心的做了準備工作,與檢察官通電話的時候,堅持面談(因為有的檢察官推辭見面)。
負責這個案子的是名三十多歲的女性檢察官,律師一見面,就很友好的說,你們這裏還挺正規的,比別的城市強多了,很快緩和了氣氛,在友好的你來我往的寒暄中,律師切入正題,講到法輪功在國際上的形勢,當前中國國內現當政者與迫害政策的切割,講到別的城市出現的對法輪功學員的案子撤訴的情況,檢察官對這點很感興趣,問:「某律師,你做過的案子有這種情況發生嗎?」這一問正中下懷,律師早就準備好了,立刻拿出自己做過的案例文件給她看。
整個過程近兩個小時,效果非常好,臨走的時候,律師以朋友的身份提醒她:「這個年頭,咱們做事都得留個心眼。」檢察官將律師送到門口,臨別了,還說了聲:「謝謝某律師」。後來在這個案子中這位檢察官兩次退案,再加上整體同修的營救,被迫害同修被釋放回家。
當然,律師的重要作用還體現在庭審時的無罪辯護,律師的無罪辯護一般都圍繞信仰無罪,修煉法輪功合法,對法輪功定罪是蓄意錯用法律等幾個主題來展開。這些對在場的人都是很好的聽真相的機會,許多參加過庭審的同修家屬聽了律師的辯護,才明白即使按照中國現行法律修煉法輪功也是合法的。可是對於那些長期被邪黨洗腦的公檢法人員,依然知法犯法、枉法判決。在這種情況下,我丈夫提出請律師反訴公檢法人員蓄意錯用法律違法判決,並另行支付律師費。可是對於這個提議,幾位律師都委婉推辭了,估計他們還是有壓力的。不過有的律師雖然沒有主動控告他們,但是在整個辦案過程中,對公檢法所有不符合法律的程序、行為均不配合,並當場揭露,這個對公檢法人員的震懾力也是極大的。二零一八年的那場非法庭審,律師在這個環節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非法庭審那天,我們去了庭審現場,目睹了整個庭審過程。律師首先做了無罪辯護,又對公安人員取證過程中前後矛盾的地方提出質疑,之後突然提出現場庭審無效,原因是當庭法官宣布檢察院公訴人名字是A,而現場實際提起公訴的是B(因為律師認識此人),律師當場指出既然B不是公訴人,那只能是書記員,而書記員是不能提起公訴的。所以根據《刑事法》和《刑事訴訟法》的相關條文,今天的庭審是無效的。律師的這個舉動,使得在場的法院、檢察院的人員都非常尷尬和被動,庭審過程均有錄像,律師陳述語速緩慢,要求書記員記錄在案。
非法庭審結束後,法官留下了律師,態度很客氣的徵求律師的意見,律師說:「以您的身份,應該很清楚法輪功在咱們國家到底是怎麼回事,你也清楚這是一群甚麼樣的人,中國國內形勢說變就變,能幫他們就儘量幫幫他們吧……」
值得一提的是,這之前,律師約見這名法官時,法官推辭不見,而現在卻能主動找律師協商,應該說律師的作為震懾了他們。因為當時從表面上看,這位同修被抄出一千多份資料,庭審公訴人建議刑期是二~三年,這個刑期一般都是他們內部事先商量好了的,最後這位同修被非法判刑十個月。應該說律師的作為使得這名法官對大法弟子的迫害有所收斂。
當然,任何一個結果都不是取決於某一個環節,它和我們的修煉是息息相關的,以上我們只是從律師發揮作用的角度來闡述這個問題,我們也不能孤立的看問題。
三、提升自己,擺正與律師的關係
前面講的都是和律師配合好的一面,其實過程中,也有很多不如意的地方。這些不如意有的需要我們修去執著心,有的需要增強包容心,有的需要我們智慧對待,更重要的一點,我們還要擺正與律師的關係。
我們悟到,律師能為大法弟子辯護,也是歷史上安排好的,他們就是以這種身份來幫助大法弟子證實法,應該說他們也是有歷史使命的。雖然他們大多是常人,但是能擔起這個使命必須也得要求他們有良好的品行道德。所以合作過程中,就不單單是一個簡單的雇佣關係,他們也是需要大法弟子救度、歸正的眾生,所以配合過程中,我們只能正一切不正的,不能因為我們的人心助長他們的不正當行為。
二零一六年的兩場官司,律師費都是我和丈夫自己出的,因此在付費額度的問題上,沒有太多顧慮。記得第一次接觸律師時,覺得他們能為大法弟子發聲,我們的心情都是感激有加,所以談律師費時,丈夫很痛快的表示:「我們經濟條件好,不需要優惠。」以前有過這方面經驗的同修提醒我們,注意珍惜大法資源,而丈夫認為是我們自己出的錢,不存在這個問題。
那兩場官司,一審下來,結果都不是很理想,我們詢問律師向中院上訴的必要性,律師表示:「上訴還是有作用的。」所以,我們兩個案子都委託該律師上訴。其實我們這裏二審是不開庭的,律師所做的工作只是郵寄給中院一份通用版本的上訴書,內容只是根據個案做一下微調,而每個案子上訴的律師費是一萬元。對此,我心裏有些想法,找機會諮詢了其他律師,他的建議是法輪功(被構陷)的案子許多地方二審並不開庭,如果只是遞交一份上訴書,由當事人自己上訴就可以了,沒必要浪費資金委託律師。如果二審要開庭,或者有特別情況需要上訴中院的,才有必要花錢請律師。
這期間還發生一件事情,先前配合過的律師在另一場官司中提出律師費要漲價,並說現在普遍都漲了,北京等地漲到一審(三個階段)五、六萬元(我們以前是每個階段一萬,路費另算)。我覺得不管是否屬實,讓我們聽到這樣的話,一定是我們的心有問題。就著這個問題,我跟丈夫交流:「律師能幫助大法弟子,也是在完成他們的使命,我們不能有感恩戴德的心,他們畢竟是常人,有人心,我們不應該助長他們『大法弟子的錢好掙』這樣不正的想法,這不是真的對他們好;另外如果助長了這樣的風氣,豈不是給那些貧困地區的同修請律師增加了負擔。」丈夫覺得很有道理,承認之前的想法不正:覺的他們頂著壓力是在為我們付出,內心有拿錢補償的想法。如果大法弟子的心都擺不正,又如何去正世人呢?律師也是在履行自己的使命,不能狹隘的理解成為我們在付出。我們擺正心態,堅持按照原來的付費標準。
後來,有律師抱怨說做法輪功(被構陷)的案子壓力大、掙錢少時,我跟他說:「大法師父說:『一個常人在這種對大法弟子迫害的今天能夠做了大法弟子做的事,這個人一定成神,即使他是常人都沒修煉。』[1]你想想在歷史的今天,你能為大法做事,這不是你的榮幸嗎?這些不是用金錢能換得來的,你應該感到無比榮耀。」他雖然沒說甚麼,但感覺他在認真思考。
二零一七年,因為案情需要,經別的律師介紹,預約了一位律師,見面前了解到有關這位律師的一些爭議,我們經過慎重思考,決定先見見面再說。接觸後,發現這位律師其實就是很有個性,不願隨著我們的思路做事,也不願多交流,但是對一些原則問題的認識是沒有問題的。既然這樣,我們就放下心來,誠心對待他。那年十二月份的一天,天降暴雪,他通知我們晚上十一點多去機場接他,結果我們在機場等了好久,才得知因本地暴雪,飛機跑道來不及清理,飛機降到別的城市了。他告訴我們說不知飛機今晚還能不能起飛,他也在等通知,要我們先回家吧。於是我們就回家了,機場到我家一個小時車程,到家時已經下半夜了。剛脫了外衣,律師發來短信,說馬上要登機了,並說如果已經回家了,就不要去接他了,他可以打車去賓館。丈夫說:「這樣的天氣,也不知機場還有沒有出租車了,反正現在也沒有睡意,還是去接他吧。」這樣我們又冒著風雪,回到機場接到律師,看的出來,他很感動。從那以後,他對我們隨和了許多,還給我們提了許多好的建議,而且非常注意我們的安全,接送他去敏感地方,他都是避開攝像頭下車。
在和律師配合的過程中,我們像對待其他世人一樣,把大法弟子的風範展現給他們,所以我們接觸的律師都對我們很信任和敬重。有一次,一位律師問起前一年營救回家的同修的現況時,我說:「其實我不認識這位同修,至今也沒見過面。」這之前他只知道我們在營救那位同修時所付出的一切,卻不知道我們和那位同修素不相識,他由衷的說:「你們這個群體是沒有人能擊垮的了。」
四、過程中的反思
幾年下來,每一場官司,我們都竭盡全力,希望能有所突破,從形式上來看,圍繞著官司,方方面面做了不少事情 ,同修整體配合給公檢法人員郵寄真相資料;粘貼營救同修的不乾膠;非法庭審前發放有真相內容的邀請函;特別是同修們整體配合發正念,應該說所做的這一切在解體邪惡、救度眾生方面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雖然這些年請律師打官司在我們證實法中有很大的意義,但是我們也看到或感覺到一些不好的現象或趨勢。雖然能為法輪功辯護的律師數量在增加,但是中共邪黨也加大了對律師的迫害,司法部內部限定律師不得就法輪功定性問題進行辯護,目前公檢法迫害大法弟子的具體依據是前兩年出台的「兩高司法解釋」,而這個「兩高司法解釋」在認定有罪的前提下講如何量刑,邪黨就是要誘導律師圍繞這個「兩高司法解釋」來辯護。其實是邪黨在給律師設置圈套:用表面的法治來掩蓋實質的迫害。
那麼在這種情況下,律師對無罪辯護投入精力越來越少,基本上都是套用固定的模式,無罪辯護的力度不夠,越來越有走過場的感覺。更有甚者,明慧網有文章披露,個別律師私下與法官達成默契:我辯我的,你判你的。與高智晟那批正義律師相比,目前有些律師的心態已經發生了變化,雖然他們崇尚正義,願意為正義站台,但是他們更多的關注自己的收益,不願觸動邪黨的底線,不想給自己帶來危險。在安全方面給自己畫了一條紅線,在紅線範圍內,怎麼做都行,超出紅線就不做了。
我和丈夫再次深入交流了這個問題,覺得律師出現這種現象和我們大法弟子整體的狀態有關係。反觀我們自己的修煉狀態,在破除邪惡方面,因為境界所限,不能真正神起來,用師父賦予我們的神的威力去徹底清除邪惡,全盤否定舊勢力從上至下安排的迫害機制,而是固守著人這一層的理,不敢也不願突破,內心對迫害無可奈何。天上人間都是對應的,我們大法弟子都這樣,還能指望作為常人的律師替我們頂著邪惡嗎?
就拿當前來說,隨著正法形勢推進,世間形勢變化也很大,發生了中美貿易戰、香港反送中等事件,好多同修動了常人心,把自己擺在人的位置上,把解體邪黨的希望寄託在常人身上。世人所做的一切,都是在天滅中共的過程中為自己選擇未來,而大法弟子是解體邪惡的主導者,而不是旁觀者。師父說:「作為大法弟子來講,也不應該把希望寄託於所謂的自然變化、外在的變化、常人社會的變化,或者是誰給我們的恩賜。你們就是神,你們就是未來不同宇宙的主宰者,你們指望誰呢?眾生都在指望著你們!(鼓掌)真的是這樣啊。」[2]
我和丈夫認識到這些後,覺得如果大法弟子沒有實質的提高,那麼請律師打官司也好,其它項目也好,就會流於一種形式,所有的項目離開了我們修煉人提升的因素,那項目本身和常人中的工作沒甚麼兩樣了。基於這個考慮,我們推掉了那些只為走過場,而沒有實質意義的官司,這樣的官司不只會浪費大法弟子的資源,還會加重同修們的依賴心,忽視營救同修中整體正念的作用。我們必須回歸到修煉提高這個最本質上來,使每一個項目,每一場官司都能在我們大法弟子的提升中展現它的價值、完成它的神聖使命。
師父告訴我們要:「修內而安外」[3]。這六場官司,表面上看是我們做了自己該做的事,實質上是師父在過程中安排我們看到自身修煉的不足,從而能夠繼續提高,更加成熟。寫到這裏,由衷的感恩師父的慈悲苦度。同時,也感謝同修們過程中無私的配合,感謝正義律師的辛苦付出,願眾生都能得到大法的慈悲救度,都能擁有美好的未來。
註﹕
[1] 李洪志師父著作:《二零零五年舊金山法會講法》
[2] 李洪志師父著作:《各地講法二》〈二零零二年美國費城法會講法〉
[3] 李洪志師父著作:《精進要旨》〈修內而安外〉
English Version: http://en.minghui.org/html/articles/2020/5/6/184353.html